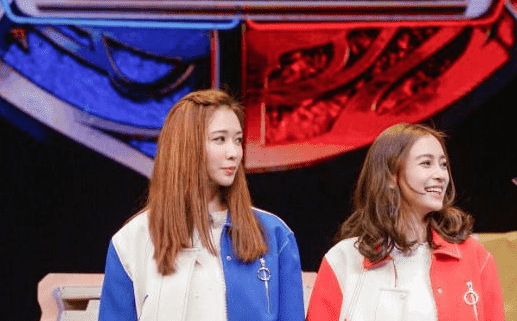“叙利亚”在罗马帝国时期,妇女在宗教参与方面,具有多大宽容度?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史说新语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妇女在宗教参与方面,具有多大宽容度?》,希望大家喜欢。

罗马帝国时期叙利亚的宗教崇拜对象主要是本土神与希腊神,他们经常会被雕刻在同一块浮雕之上,或在一个神的身上表现出不同文化的元素。
霍姆斯郊外出土的一块浮雕上就雕刻着三位不同文化的神,分别是叙利亚北部传到帕尔米拉地区的月亮神阿格利博尔、雅典娜,以及穿着叙利亚服装的克诺索斯。
在地中海世界文明交往的背景之下,叙利亚人的崇拜是本土崇拜、希腊崇拜与罗马崇拜的结合。
在这之中,对于最广大的普通妇女来说,她们更关注本土神和希腊神。
一方面,罗马推崇的神是希腊神的变体,在地方上,对于罗马神的理解是在希腊神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罗马推崇的皇帝崇拜、罗马起源神话的崇拜等的影响更多集中在殖民大城市,并且与政治仪式和政治话语相结合。
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妇女来说,她们基本不被允许参与这些政治目的的宗教仪式,罗马神对她们的影响因此没有本土神和希腊神更大。
叙利亚妇女崇拜的本土神灵主要是赋予生命的女神、人类和动物的母亲保护者阿塔伽提斯,她被等同于阿尔忒弥斯、阿芙洛狄忒、希腊命运女神堤喀或罗马命运女神福尔图纳。
阿塔伽提斯的主要祭祀中心在叙利亚北部的班比斯,也被称为希罗波利斯,意为“神圣之城”。
在班比斯的阿塔伽提斯神庙里,女神由狮子支撑,手持权杖和纺锤。叙利亚出土的亚历山大到罗马时期的货币,都一致地显示女神是狮子神,无论在何处,她都是坐在狮子或狮子王座上。
在杜拉·欧罗波斯发掘的阿尔忒弥斯·阿塔伽提斯神庙中的座位上,刻着一排排名字,其中大部分都为女性名字。
这可能表明,在阿塔伽提斯的神庙中有某种独属于妇女参与的宗教活动或独属于妇女的宗教空间,刻字是为她们的参与所预留的位置;这些名字也可能是对神庙奉献者的铭刻,因为一个名字经常不止占据一个座位的空间。
无论是哪一种,都证明叙利亚妇女在阿塔伽提斯崇拜中的参与程度不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女性名字可能来自相同的精英家庭,只有精英家庭的妇女可以在崇拜仪式中拥有固定的座位。
并且对于女性血统的强调或许也证明在叙利亚虽然家庭、祭祀、财产等按照男性世系传递,但女性血统也很重要。
在叙利亚,阿塔伽提斯的配偶通常是巴鲁,至少从公元前三千年起,风雨之神和战士之神巴鲁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接受崇拜。
巴鲁神的崇拜是西闪米特崇拜体系的核心,公元前24世纪的埃勃拉遗址中就出现了可以被识别为巴鲁的神。
巴鲁神的崇拜带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崇拜的痕迹,埃梅萨的巴鲁神塑像是一块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巨大圆锥形黑石。
在罗马城的巴鲁神庙里,也矗立着两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雕像。在罗马本土的巴鲁神祭典中,会有一群叙利亚少女围着祭坛跳舞。
在帕尔米拉,巴鲁也被称为贝尔,出土的帕尔米拉贝尔神庙上的壁画显示,当叙利亚妇女观看贝尔崇拜仪式时,她们需要戴上面纱。
这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妇女参与宗教时存在某种禁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叙利亚妇女在公共场合的惯常装束。
贝尔神庙中男女信众共同参与观看的崇拜仪式通常被解释为神像的到来和圣所的落成典礼,这证明,帕尔米拉的妇女可以参与神庙的重要宗教仪式,但神庙壁画中男女信众被分别描绘在两侧的墙壁上似乎也证明男女两性在宗教场合中的隔离。
叙利亚妇女崇拜的本土神还包括腓尼基神巴尔夏明。巴尔夏明神庙的铭文显示,神庙有记载可循最早的两次献祭都是由女性完成的。这两位女性为她们自己、自己的儿子以及兄弟向神明献上两根神柱。
显然她们都结婚了,但祭祀的受益人却是她们的儿子和兄弟,并不包括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叙利亚的妇女虽然因为婚姻的关系而属于丈夫的家庭和部落,但女性的奉献可以使她们与原生家庭保持一定的联系。
除了为儿子和兄弟献祭,其他妇女的献祭铭文中也会包括丈夫、子女,甚至还有单独的女儿。
与男性献祭铭文相比,这些文本类型在碑文语料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现有数据表明,女性在宗教献祭领域的存在是有限的。但是,在巴尔夏明的祭祀中,妇女有时候也会主导一座祭坛的修建,并且可以为自己树立雕像。
在帕尔米拉,对匿名神的献祭中,最主要的大型贡品也都是由女性奉献的。叙利亚妇女还崇拜腓尼基神塔姆兹。
塔姆兹每年都要死去,在他死去的时候,植物枯萎,动物和人类停止繁殖,所有的生命都受到威胁。
在诸多叙利亚出土的文物中,塔姆兹经常手持植物来象征夏季的结束。后来在其配偶伊施塔尔的帮助之下,塔姆兹才能重回人间。
塔姆兹的神话就是腓尼基人对自然现象的神话性解释。后来希腊人吸收了塔姆兹的神话,塔姆兹开始被称为阿多尼斯。根据萨莫萨塔的琉善的记载,在罗马统治时期,叙利亚人自己也将塔姆兹神称为阿多尼斯了,伊施塔尔配偶身份也被阿芙洛狄忒取代。
叙利亚少女总是年复一年的哀叹阿多尼斯的命运,在比布鲁斯,她们在仲夏时节举行对阿多尼斯的秘密祭典。
在第一天的阿多尼斯哀悼仪式中,妇女们伴随着尖锐的笛声哀嚎、哭泣;但在第二天,她们又会庆祝阿多尼斯的回归,妇女要剃掉头发以示尊敬,而那些想留头发的妇女必须在广场上向陌生人献身,以示忏悔,而为她们的服务支付的钱被供奉给了阿芙洛狄忒。
在帕尔米拉的庆祝阿多尼斯回归的仪式中,也会有女歌手为众人献上表演。阿多尼斯的崇拜仪式发挥了宗教的补偿功能,在崇拜活动的秘密祭典中,妇女可以通过某些平时不被允许的方式放松,成为一种缓解精神紧张状态的手段。
阿多尼斯的奉献仪式中还存在专门储放酒的空间,或许可以证明叙利亚妇女在阿多尼斯崇拜仪式中打破了饮酒的禁忌。
并且,由于阿多尼斯崇拜仪式大部分时候都只向女性开放,女性由此获得了社会性交往的补偿,她们可以参与庆祝活动,通过彼此的交往,交换信息,创造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友好环境,在其中可以有短暂的放松时刻。
以秘密仪式为核心的崇拜在罗马地中海世界广泛存在,在叙利亚,妇女参与的秘密宗教仪式还包括对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埃及女神伊西斯、波斯神祇密特拉的崇拜仪式。
叙利亚人的崇拜并不排外,他们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神灵。和这一时期的地中海其他非一神教民族一样,用自己的语言和神话体系解释其他民族的神,将对方的神与自己崇拜的神结为配偶。
希腊的德洛斯城提供了大量的碑文证据,表明叙利亚人广泛参与了希腊和希腊式的宗教祭仪。
叙利亚妇女崇拜的希腊神主要是阿尔忒弥斯、阿芙洛狄忒以及宙斯。对阿尔忒弥斯与阿芙洛狄忒的崇拜显然是因为她们被看作是阿塔伽提斯的希腊版本,她们经常会与阿塔伽提斯一起在同一个神庙内被崇拜。
宙斯也被看作巴鲁或贝尔的希腊版本。20世纪三十年代,在杜拉·欧罗波斯发掘了一座供奉宙斯的神庙。在那里,他可能是阿塔伽提斯的配偶。
在宙斯神庙中,神被描绘在后墙的壁画上,侧面的墙壁上则绘有宙斯的男女朝拜者。朝拜者以祈祷的姿态举起右手,或在火炉上洒香。
同时,在神庙中,还绘有当地精英家族的画像,其中也包括精英家族中的妇女群体,被识别的就有一个名叫巴利波尼亚的妇女,她佩戴着头饰和一系列奢华的饰品。
叙利亚妇女通过参与神的崇拜参与了一定的社会活动,她们可以参加庆祝活动、观看游行、参与祭祀,甚至在某些地方可以主导一次献祭或者祭坛的修建。
但铭文文本证明,叙利亚妇女主导的献祭是有限的,她们大部分时候的参与都只是群体性的,她们也不被允许参与神庙和神庙经济的管理。杜拉·欧罗波斯的证据表明,所有的牧师都是男性。
根据罗马人的观念,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某种特殊神灵的帮助,而这种神灵的职责就是促进这种特殊形式的活动。据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瓦罗能够列举出三万名这样的男神和女神。
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任何事情都有其主导的神,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进行祈祷和致敬,不仅是国家大事,也包括吃饭喝水的小事。
这就是说,宗教不仅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也在私人领域中发挥作用。叙利亚虽然没有罗马这样多的神,但基本逻辑是相似的,即普通人参与宗教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并没有实际影响神庙事务或其他公共决策。
叙利亚妇女的宗教参与实际上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人片刻地进入到公共领域参与共同的社会活动,对公共领域其实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宗教也是现代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重点在于通过对神话、隐喻、教条的分析来揭示宗教作为特权阶级想象的产物是如何模糊或污名化妇女在现实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存在,并且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恢复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以重新书写男性中心的传统宗教。
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哲学家伊丽加莱,她的论文《神圣女性》就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象征世界,以使女性能够理解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而不是仅仅作为与男性主体相关的对象。
女性主义因此从研究妇女的宗教参与、基督教内的女性运动、父权制对宗教中女性形象的扭曲的女性神学转向解构父权宗教、构建妇女的宗教话语和符号体系的女神学。
女神学虽然最早主要探讨基督教内的性别制度,但以女性为主体,解构传统宗教,发掘传统宗教中的女性经验,建构新的女性主义的宗教是一条可以参考的研究一切父权制社会宗教的路径。
比如希腊罗马的主神以男性主神为中心,是一种永恒的父权制在宗教中的表现,而叙利亚等西亚地区的大女神的崇拜则是女性特质在父权制社会的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