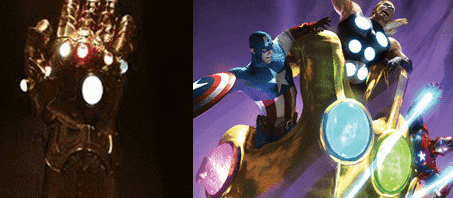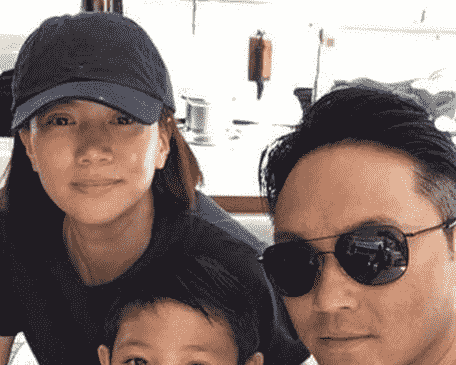“宗室”从汉、唐、宋等朝代,分析古代宗室管理的变化!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徐玉婷的《从汉、唐、宋等朝代,分析古代宗室管理的变化!》,希望大家喜欢。

“古代中国的政治史里,皇帝处在中心位置,这当然是常识,可恰恰是因为常识,而往往被忽略”。
皇帝是整个国家机器开动的核心,但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需要涟漪般一圈一圈的利益共同体来管理国家、巩固统治。
在宗法制社会下,血缘关系决定皇族就是这涟漪中最靠近中心的那圈,也只有这一圈荡成一个完美的圆环,才能使滴水的力量传得更远。
从历代宗室管理制度优化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圈禁就会明白,皇帝需要把权力牢牢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定伴随着对宗室全方位的控制。
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开始,宗室最主要的作用就在于拱卫王室。刘项相争时,刘邦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后又封同姓九王,造成中央政府与封国长时间的对立。
为牵制诸侯王势力,汉初使郡国杂处,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七国之乱的爆发加快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进程。汉景帝中元五年改革诸侯国官制,此后,皇族的管理权被收归中央,由九卿之一的宗正管理。
武帝即位后,颁“推恩令”、设附益法,置左官律,由朝廷派官员管理封国事务,剥夺了诸侯王的行政和人事任免权,使其逐渐成为“不与政事,衣食租税”者。
东汉对宗室的限制更为严格,明帝封诸皇子为王时,以“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为由,削其封地和岁入,诸侯王子们多封为仅食租税的乡侯、亭侯。
西汉宗室的定义较为宽泛,除了皇帝的同姓宗亲,还包括皇帝和诸侯王的后妃家族。景帝改制以前,各诸侯国都有相对独立的宗室管理体系,赏罚也就相对灵活。
宗室统管于中央后,宗正管理宗室属籍,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有属籍者”和“无属籍者”。封赏通常赐予有属籍的宗室成员,他们还享有法定特权,如免役权、犯罪后的“先请”权等。
到汉武帝时期,宗室人口大量增加,武帝以儒家“五服”学说为标准确定入属籍者,五服以外的宗室则不再受特权法保护。
对谋反的诸侯王,以诛杀或迫其自杀为主,牵连其中的宗室削其属籍,但也有机会得到皇帝加恩恢复。诸侯王的普通犯罪不过分追究,而王子侯若有类似的犯罪行为则往往受到较重的惩罚。
与其说他们享有多大程度的实体法上的特权,不如说他们所享有的更多的是程序法上的特权。
过于严苛的监视引起地方诸王对中央的反叛,统治阶级内部的动乱使宋齐王朝迅速崩溃。
宗室广泛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立下赫赫战功。为改造魏晋以降浓厚的门阀观念,太宗通过“造就新的门第观念与宗法制度,抬高李唐宗室与官爵的地位,以利于维护本朝统治。”
同时,经由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的他深知宗室的潜在威胁,于是降封宗室爵位,诸王外刺,不再让他们进入权力核心。
从宗室阶层的任官品级来看,“唐前期的宗室仍不脱浓厚的贵族气息,……官职不过是他们贵族身份的外在表现而已。”
武则天统治时期大杀宗室诸王,李贤之子“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这一时期的争斗对唐代发展影响甚深,玄宗就是在这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
“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阁,虽以国王之名,实与匹夫不异。”玄宗待宋王成器等人极尽亲亲之谊,但“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
又派家臣宦官充任十王宅使,负责管理宅内诸王的起居,实际上也就是集中监视。
此外,宗室诸王册封被削减,结交外臣、私自出京都是被禁止的。将宗室置于皇权严密控制下令其集中居住这一行为,并非玄宗首创。
据孙英刚先生考察,隋惩北周宗室不竞,出于土地利用和政治控制的考量,重新规划了城市布局,诸王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监管十六王宅的宦官权力膨胀,甚至操纵皇帝的废立。
安史之乱中,“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德宗以后,国家多难,皇帝自顾不暇,宗室自然每况愈下。
唐代宗室的范围较广,除了皇帝诸子以外,皇后的亲戚、受赐李氏远亲、赐姓功臣也准入宗正寺属籍,视作宗室。
唐代“宗室”所涵盖的人群虽宽泛,但规定“过五等者不为亲”,五服以外亲属被分赐田地,送外首都之外的地方自食其力,等同庶民,所以国家奉养的人数始终是可控的。
玄宗对宗室的一系列控制,使宗室不再有能力挑战皇权。然而,将宗室几乎完全弃之不用的做法也对唐后期的政局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作为因亲而贵的宗室,他们天然是皇帝触角的延伸,而高爵级宗室被从外刺地方召回豢养在十六王宅,等同于斩断了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网络,只能在叛乱中坐以待毙。
宦官控制王宅,也控制着帝国未来的主君,玄宗以后,皇帝难以操控这股力量,最终遭到反噬。
有鉴于此,宋代对宗室政策在承袭唐代的基础上做出了调整。在宗室划分问题上,太祖赵匡胤三兄弟的所有子嗣皆为宗室,五服之外的亲属仍在宗室之列。
然而,自太宗始,亲王皆序位于宰相之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皇子封王的数量极少。在爵位继承上,他们被授予有名无实的官衔,享受着美爵厚禄,唯一的职责只是“作为一个有形而无声的整体出席朝会。”
宗室诸王聚居,为防止往来过密和交结外官,两宋推行比唐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不仅有会见禁令,还设敦宗院,派专人监视。宰相卢多逊曾因“交通秦王廷美”被罢相。
帝国的第四代宗子突破千人,仁宗在宗正寺之外新设大宗正司,由出身显赫的宗室担任知宗正司事,管理行为失范的宗室。
元丰改制,诏大宗正司不隶于中央六曹体系之内,明清宗人府的设置亦滥觞于此。北宋开始,宗室犯罪除了罚赎、降级、贬谪、除名、诛杀之外,幽禁在宗室处刑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按情节轻重分为居住、拘管、监管和锁闭。
他们被幽禁的原因不一,可见,宋代的锁闭与清代圈禁同是对宗室犯罪的缓刑规定,但它没有根据犯罪类型和轻重程度不同区别处刑,而是统一以三年为限,届期请旨。
这样的制度安排对罪过较轻的宗室而言不公平,也无法起到对重罪惩戒作用;皇帝虽把宗室的刑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却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
相比之下,清代在这一点上有所进步。唐末宗室的悲惨境遇、宋朝宗室“举族南迁”与元末河北军阀察罕帖木儿等人拥军割据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防范京官擅权、平定边境战乱,希望像周一样国祚绵长的太祖也沿用了分封诸子的做法,可惜事与愿违,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宗室成为贻害帝国的三大祸端之一。
明代宗室的地位与收入远在诸臣之上,以亲王为例,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十岁封为王世子,长孙立为王世孙,冠服视一品;亲王余下诸子年满十岁封为郡王。
明代封爵世袭罔替,一个亲王的岁禄约是一品大员的十倍,爵位最低的奉国中尉岁入也多于正五品官员,是正九品官员的三倍。
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付出数十倍于养官、养廉的赋税收入,去养活宗室这个日益庞大的寄生阶层。
明初,诸王手握重兵,坐镇四方,烜赫一时。他们藩屏的使命完成后,自建文朝至天顺朝,宗室的权力和财富被不断蚕食:诸王典兵之权收归中央、禁止干预地方行政、禁止宗室出城和二王相见,更不准来京奏事、科举入仕。
不同于宋代“宗室犯罪,不以亲疏、有无官爵,罪犯轻重,从来循例,与常人同法”的政治口号,明代直接在律典中载明,宗室“虽有大罪,亦不加刑。”
罪不加刑并非既往不咎,而是延续了宋代的刑罚方式,包括罚俸、革爵、羁押和赐死。明代安置罪宗的方式有四种,分别是关押于凤阳高墙、伴守祖坟、拘禁闲宅和府内闲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高墙之制。
凤阳是大明祖陵所在地,也是“龙兴之地”,为使罪宗反省悔悟而将罪宗发往,因人数陆续增多便在此地修筑了专门关押宗室的监狱。
高墙本用于关押身患重罪之人,后来程度较轻的犯罪也被送入高墙。高墙拘禁的刑期由皇帝决定,并无制度规范,甚至没有宋朝三年届满请旨的规定,一入高墙自动革爵除名,终老于此。
嘉靖以前,罪宗家属须随同前往,生活、子女婚配皆在其中,造成了大量的人口积压。与宋代一样,高墙的监管还是主要依靠宦官,但监狱外有专门修筑的防御工事和专职护卫的高墙军。
由此可见,对宗室的倚仗与防备历代皆然,各朝统治者都在不断探索宗室治理的最佳方案。
自唐以来,对宗室已有囚而不杀之惯例,宋明处理宗室问题也延续了这一思路。
大清建国之初,宗室犯罪与平民一样要受鞭刑、戴刑具,他们没有皇亲一体的概念,但在汉族士大夫眼里,这一“有伤国体”的行为不能被接受,顺治帝福临方意识到宗室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保护。
清军入关前优待宗室的种种制度,并不是按照儒家等级观念和伦理思想制订的,其保护范围也仅限于宗室贵族,而随着宗室人口增多,按照儒家“亲亲尊尊”的传统,这部分宗室的法律特权也需要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