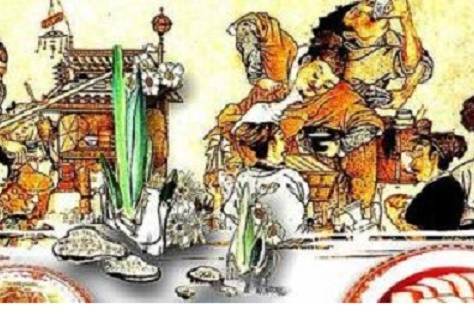“王羲之”生前断绝名利,死后却被封神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最爱历史的《生前断绝名利,死后却被封神》,希望大家喜欢。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掀起了一场造神运动。
这位戎马半生的皇帝受翰墨熏陶极深,素来喜欢挥毫作书,而他心中最爱的一位书法家,正是王羲之。为了一睹偶像的真迹,他斥重金搜求王羲之的墨宝,史载“大王真书惟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并以金宝装饰”。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稀世之珍来到皇宫之后,被精心剪裁装裱,秘藏于内府,就像进入了神坛的祭品。平日里,太宗将王羲之的真迹置于座侧,日夜观览,意犹未尽时,定要亲自临摹一番。有时候一个人欣赏总觉得不够,他便多次拓印《兰亭序》赐给左右重臣,有乐同享。
帝王的趣味确能通过权力的毛细血管扩散到各个领域。要知道,王羲之的书名虽然显赫,但在其死后,名气甚至还不如儿子王献之。而在李世民狂热地推崇之下,王羲之俨然已是一代书圣,天下文人莫不效仿王羲之的笔墨。当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已是书法大家,却也不得不迎合人主所好,奉王书为正宗。
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将与王齐名的张芝、钟繇等人通通斥为不值一提的“区区之类”,却给右军留下了一句“尽善尽美”的评价。百花齐放固然好,但是在统一的大帝国面前,只需要一种能够彰显盛唐气质的艺术典范。王羲之的作品无疑最为符合盛唐的文化气象:包容南北,推陈出新。
十年之后,唐太宗逝世,《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末之乱,有一个叫温韬的武人掘盗唐陵,关中地区的陵墓纷纷遭灾,其中的书画被一抢而空。李世民与王羲之的缘分似乎在唐帝国的覆灭中烟消云散,可是王羲之的美名却依旧留了下来,此后历朝历代,书圣之名从未易主。
唐太宗。图源:影视剧照
权力的推崇并不是王羲之成为书圣的唯一原因。
事实上,王羲之的书法似乎有一种永恒的亲和力,它从江南水乡的土壤中诞生,经过东晋玄风的吹拂,以及士族气质的洗涤,本是极具时代风格和个人烙印的作品,却能和每个时代的人产生共鸣,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
即便在今天,依然找不到一件王羲之的真迹,在历史的蛛丝马迹之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个来自1700年前的书法家的魅力。他就像一座高不可测的山峰,你愈是向上攀爬,愈是觉得神妙无穷。
01
杜牧《润州二首》其一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而王羲之就是最为典型的晋人风度:高门大姓,性格耿直,超尘脱俗,寄情山水。
他在八王之乱中降生,还没有和北方土地产生紧密联系,便跟随家族——琅玡王氏来到了江南。他的父亲叫王旷,是第一个向司马睿提出镇守江南的人。出身于如此位高权重的一个大家族,王羲之自小便和能够左右一朝风向的人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他的伯父是王导、王敦,岳父是郗鉴,同时又与庾亮、庾翼兄弟关系不错。
身处在权力网络的中心,他自小就被烙印上了文化精英的气质。
史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王羲之的早年轨迹和大多数自诩旷达的东晋士人相同:名声响彻在外,受征召不去,辞官几次之后,便走马上任。一开始,王羲之在庾亮的帐下任职,庾亮虽然与王导是死对头,对王羲之却非常好,临死前还上书朝廷,称赞羲之,为其打点官途。
王羲之后来也投桃报李,在庾翼准备大举北伐之时,给晋康帝上了一道奏折以示支持:“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北伐对于东晋朝廷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丧乱之初,北方士人跌跌撞撞来到江南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外面是异族势力的窥视,里面是江南土著的排挤,他们难免想念故乡。当东晋朝廷扎下根后,人心思定,覆亡的痛楚被抛之脑后,回望北方的眼神已然变了。相比回到烽烟弥漫的北方,他们更愿意呆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寄情于山水之间。
王羲之是慢慢体会到这种矛盾的心情的。
庾亮之后,桓温上位,东晋任命殷浩为扬州刺史以制衡桓氏。扬州刺史殷浩对王羲之的才华很赏识,多次劝他出山。王羲之回信道,与其做一个护军将军,他更想做一位使臣出使四方,前往关西、陇右、巴蜀之地,宣扬晋德。
后来他还是接受了护军将军的职位,并且写信劝诫殷浩和桓温修好,不要内斗。永和八年(352),殷浩决意北伐,这一次,王羲之摇身一变,成了最积极的北伐反对者。在那些年,他数次上书反对北伐,直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甚至劝殷浩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
这种言论已然是十足的消极。不过,此时的东晋朝廷也确实不适合北伐,内部斗争不休,外部也缺乏良将。殷浩北伐遭致大败,被废为庶人。王羲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畅不已。”言下之意,殷浩的失败,给桓温清洗朝堂,以武力把持朝政提供了机会。
在担任会稽内史的任上,王羲之也注意到了地方上的顽疾:中央的命令朝令夕改,下层官吏贪污枉法,百姓身上背负的赋役如同一座大山,被迫离家逃亡。王羲之想要做一些事,比如推行禁酒,节省粮食,可惜无人支持。他也注意到了地方豪强吞并贫民田土,躲避赋税的现象,却无力改变,毕竟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像琅玡王氏这样的大家族。
总而言之,王羲之的为官之路非常不顺心。大人物的斗争,地方的盘剥,都是无解的问题,而他能做的便只有叹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流露出非常颓废的一面:自己来做这没意思的官,纯粹是找罪受。精明且富有韬略的政治家,和追求个性的艺术家,这两者在绝大多数时候无法兼容在一人身上。
现实生活是永远没法旷达的,王羲之唯有超然物外、追求己心,与其纠结于顽疾难除的社会政治,深陷于儒家事功对自我的禁锢,不如寄情山水、钟情艺术。
王羲之画像。图源:网络
02
书法是王羲之栖居心灵的场所之一,在黑之线条和白之素纸之间,他找到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王羲之的书法,有一个明显的成长过程。
早年的他笼罩在书法家族的阴影中,努力汲取着前人的养分。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善行书和隶书,叔父王庾擅长书画。在两位父辈的启蒙下,王羲之自幼勤习书法,七岁时已经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蔡邕的《笔论》。聪慧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练习,池水尽墨,王羲之的书法才算入了门道。
其后,王羲之得到卫夫人的进一步教导。他自己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他先是从卫夫人学书法,后来自嫌流俗,于是主动跳出藩篱,游览名山大川,求师于前人留下的碑版。可见,他一直都有变古的精神。
当时,王羲之的书法不如当时的名家庾翼、郗愔。庾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王羲之)书,须吾还,当比之。”庾亮也曾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却说:“(庾)翼在彼,岂复假此!”
一天,庾翼在庾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庾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大为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随着年岁的增长,王羲之在书道变革之路越走越远,终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面目,完成了从“古质”之旧体,到“今妍”之新体的转变。
东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书体朝着简便实用且能表情达意的方向发展。当时流行的书风是隶书和楷书,行书正在定型,草书从章草演变为今草。开创时代的先锋正是王羲之。他众体皆备,且都入神妙之境界,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远宦帖》等。
王羲之对自己评价甚高:“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意为我的楷书可跟钟繇分庭抗礼,草书则与张芝不相上下了。这并不是一种傲慢。
王羲之像。图源:网络
他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重视线条的自然生动,这代表了一个阶层的雅好,时代精英的审美风尚。晋人素来尚意重韵,《论书》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线条的错落、空间的疏密、笔墨的曲直,就像音乐的节奏,起伏之间,可以传达出作者委婉难言的心绪。
这是书法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必然。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可以说,王羲之的笔墨之间,是那一代人追求精神自由留下的足迹。
03
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与群贤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赋诗饮酒,之后作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当时的政治情势十分和缓,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虽有桓温、殷浩等人意欲北伐,但是他们目的都不是收复失地、统一天下,而是借此立威。身在后方的士族精英们一如既往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兰亭集会选择的时间是上巳节,这本是祈福消灾的传统节日,却因为一件事而有了特殊的意义。西晋末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江南士族不服,王导和王敦导演了一场上巳出巡的戏码:“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此事之后,江南归心,东晋朝廷安稳下来。
《兰亭序》褚遂良摹本。图源:网络
恰好在这一时节,暮春的会稽山水展现她最生机盎然的一面,安居江南的诗人、政治家、哲人和艺术家们可以在山水之间躲避现实生活的苦痛和忧患,将身心沉浸于自然美景中。参与集会的诗坛领袖孙绰作诗云: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流风轻拂水面,白云荫庇着沼泽。竹林中可以听见鸟语,湖水中可以看见鳞戏。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有人将潘岳的《金谷诗序》与《兰亭序》相比,将王羲之与石崇相比,王羲之听说后十分高兴。金谷园为西晋石崇的庄园,元康六年(297年),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聚会于此,宴游赋诗,作了一篇《金谷诗序》。
只不过,《金谷诗序》的背后是礼送征西大将军石崇的荣耀,是“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的奢靡,是“昼夜游宴”、“鼓吹递奏,声伎相伴”的享乐。西晋的建立是一种表面的繁荣,在这种繁荣背后,士人们目睹嵇康等人被杀的悲剧,感慨生命无常。与其在意身前身后名,不如抓紧时间及时享乐。潘岳便是这样一个追名逐利之人,他得势之后,其母劝他知足,却终不能改,最终遭遇惨祸。
石崇像。图源:网络
与西晋士人相比,王羲之们偏安一隅,帝国的恢弘和财富的奢靡对他们来说已是过往,他们只能将躁动的心灵投向自然,恬淡自适,物我两忘。
虽然《金谷诗序》也提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晋文人对生命不永、富贵易凋的感伤和忧惧。而东晋士人走得更远,声色犬马不再是他们的唯一追求,他们在自然中仰望宇宙之广阔、之永恒,俯视人生之短促、之无常,这种悲伤带有深层的哲学意味。
就算知道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道理,还是止不住地感受到生命的虚无。这样的精神困境属于每一个东晋士人。
《兰亭序》宋拓定武本。图源:网络
04
可是,东晋士人真的完全能够忘怀一切,摆脱凡俗的生活吗?
在他们追求山水、不撄事务的背后,其实依然还有执着、贪婪的一面。旷达和不旷达,常常共存于他们的内心。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王羲之与太傅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极目远眺,悠然地遐想着,想要远离世俗。王羲之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言辞之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对夏禹和周文王的敬仰,以及对因空谈而荒废政务的厌恶。
谢安回答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似乎二人政治态度与理想是截然不同的,王羲之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务实派,而谢安是一个善清谈、无经济大略的典型。可是,当谢氏家族的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退出政坛之后,谢安便只能从自家广袤富裕的田园中出来,主持大局。
因此还有人嘲笑道;“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家族与庄园是东晋士人两个隐形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又怎么能够在天空自由翱翔呢?
谢安像。图源:网络
由于琅玡王氏的没落,王羲之并未在政坛有大的动作。自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出任秘书郎开始,他一共经历了约三十年的仕宦生涯。在他年过五十的时候,王羲之决定辞官,原因主要是他和太原王氏子弟王述的矛盾。
王述年少时与王羲之齐名,但是王羲之十分看不起他。一开始,王述在会稽做官,因母丧守孝,留居会稽,王羲之则取代王述在会稽做官。他只去王述家吊问过一次,从此再也不往。王述每当听到角声,以为王羲之来问候自己,便洒扫干净接待王羲之,多年来一直如此,而王羲之竟从不探望王述,两人的矛盾就此种下。
后来,王述升任扬州刺史,就职前走遍会稽郡,独不拜访王羲之,临出发前才辞别王羲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对佳宾好友说:“王怀祖只能做个尚书而已,到晚年可做个仆射。再想谋求会稽这块宝地,恐怕就难了。”等到王述官位显赫,王羲之耻做王述的下属,派人上朝廷,请求把会稽郡改为越州,以脱离扬州管辖。
两人之间的龃龉还有很多。
王述是个急性子,有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扎鸡蛋,没有扎到,便十分生气,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他接着从席上下来用木屐踩,又没有踩到。他愤怒极了,又从地上拾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王羲之听到后大笑道:“即使安期(王述父亲)有这个脾气,也没有可取之处,何况是王述呢!”
王述像。图源:网络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是一位性格乖张、任性使气的贵族官员,全无名士的逍遥放达。
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从今日开始,断绝名利之念。如果日后改变此心,贪图财利谋求官禄,就是目无尊长而不配做父母之子,天地所不容,名教所难恕!坚定的誓言,有如天日!”这并不是王羲之负气突发的想法,也许从多年之前对烦琐尘事的叹息开始,他便有了奉身而退的念头。
一个虽然不那么“达”但努力追求“达”的艺术家,终究还是要回到这条归隐自然这条路上来。
辞官之后的王羲之,慕仙向道,追求服食。王羲之书帖曰:“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五石散虽有暂时缓解病痛之功效,却不能多食,容易对服食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服食并没有给王羲之带来健康,反而使他长期陷入难以治愈的病痛状态。
在痛苦与安静交织的晚年,王羲之真正体会到了生命无常。
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超然物外呢?于是,他对谢万说:“常常仰慕陆贾、班嗣、杨王孙的为人处世,追寻他们无为清静超然物外的风范,乃是老夫毕生的心愿。”
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离世,也不知在会稽的山野之间体味死亡的时候,他是否参悟了旷达的真谛。
05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真正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
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献之年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羲之笑而不答。
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感悟到士人在书法上的的务简、求美之心,于是提出将“伪略”(简洁多变)与“草纵”(连绵纵引)结合起来,追求一种顺畅自然的新体。
王献之也是典型的东晋士人风格,不过更加不羁,他的书法也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有着与大王不同的美感。而且献之也对自己的书法特别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王献之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反驳道:“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
《鸭头丸帖》被认为是王献之唯一存世的真迹。图源:网络
王献之的书法是晋代书法的另一座高峰,而他也与其父并称为“二王”,代表了中国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
南朝之时,王献之的书名甚至一度高过王羲之。后来,梁武帝扭转这种尊小王贬大王的局面,把当时书法界“王献之——王羲之——钟繇”的座次,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接着,便是李世民将王羲之推为书圣。从此之后,但凡是好书画的皇帝,大多推崇王羲之。
宋代之后,由于刻帖技术的发展,社会上收藏大王墨宝蔚然成风,从帝王贵胄到公卿士子,甚至一般市民,都热衷此道,这成为南宋收藏界的一大奇观。王羲之的书法也从宫廷走向了市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当然,魏晋风度早就消散于历史的光尘之中,这种根植于士族的时代精神随着唐宋之变丧失了生长的土壤。但是,真正的艺术却是不会死的,蕴藏在王羲之书法下的美感,也会照见每个时代的“达”与“不达”。
参考文献: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
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雒三桂:《王羲之评传》,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王岳川:《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孙明君:《兰亭雅集与会稽士族的精神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吕文明:《走向神坛:<兰亭序>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造就》,《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