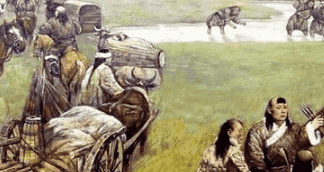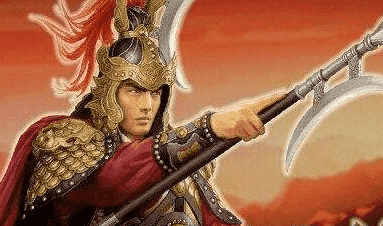“遗址”让昭陵六骏“团聚”是他的未了之愿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红星新闻的《让昭陵六骏“团聚”是他的未了之愿》,希望大家喜欢。

在野外工作是很辛苦,但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在考古队。
我每天都能记起在考古队的点点滴滴,发掘时的喜悦,一起坐在土堆上看到的最美的夕阳,甚至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口肉的感觉,都很清晰。
10月21日,考古学家石兴邦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10月23日,石兴邦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举行。
01
1923年出生在陕西耀县的他,原本的名字是“勤学”,是奶奶给他取的,到读中学的时候老师给他改为“兴邦”——那时的中国,外敌入侵,战乱连连,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向强盛。
后来他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对我的期望,我一生都不敢辜负这两个名字,只不过,我所做的并非是兴国大业,而是拿起考古铲子。
青年时期的石兴邦
石兴邦先后主持了西安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二期、法门寺地宫等重要考古发掘。但结缘考古,却有点偶然,他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时,在这里遇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夏鼐喜欢带着学生一边发掘一边学习,这让石兴邦很感兴趣,于是他“跳槽”到了考古学。
一年以后,夏鼐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也跟随前往,开始“边学习边工作”,那是1950年9月5日,石兴邦记得很清楚,也把这个作为正式加入考古的日子。在那段百废待兴的日子,石兴邦这一批考古人成长很快,1951年,北京颐和园西边要搞城市建设,他便主持过明代皇帝嫔妃墓葬发掘迁移的工作。
那次考古工作,石兴邦拿过嫔妃的凤冠一掂量,居然有好几斤重。他说:“看来,做个娘娘也不容易,戴着那么重的凤冠在宫廷上走来走去,脖子肯定不舒服。”
02
1954年,31岁的石兴邦主持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发掘成果震惊中外。这次发掘,颇有些偶然,他在考古勘探中走累了,就找个土坎坐下,无意中发现河对面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考古人喜欢这种断崖,因为不要动手“做”就很完美地展示了地层,土层堆积一目了然。
走近一看,地下还散落着一些碎陶片,“当时,我手里拿着的那一小块,显然是经过古人精心打磨的陶质片状物……如果这些陶片遇到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一般民众也绝对不会关注。于我个人来说有运气(成分), 那运气很大。”
那个年代,考古学体系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半坡遗址开始发掘后,石兴邦决定改变苏联那一套工作方法——了解文化层堆积,将器物取走就算完事。他认为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应该采用全方位探测,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 再做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第二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半坡遗址发掘现场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法,“半坡考古范式”,这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正是这种方法,第一次揭露出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发现了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上万件,认识了包含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的聚落布局,确认这是一处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王仁湘在《半坡的意义》中写道: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而且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端。
多年以后,石兴邦面对访问者回忆当年的发掘,依然记忆犹新。比如那个人面鱼纹盆,实际上是墓葬瓮棺上的盖子,里面葬着夭折的孩子:打开瓮棺的那天,我仔细揭开陶罐盖子……几个鱼的图案,巧妙地头尾相接起来,却只有一个人样面孔……盖子里面没浸土,那些图案就跟新绘上去的一样,非常鲜艳。盖子上那个眼,我想是叫小孩的灵魂出来。出来以后,可以和母亲在一起……他们用图腾神保护他们的孩子。
尖底瓶也让石兴邦难忘:他们使用的尖底瓶,无论陶质细腻程度,还是外形美观精细程度,一直到入水自动倒伏灌水的物理原理利用,让我们都惊叹不已。
考古发掘展现出来的史前时的生活场景,能看出居住在浐灞河边的部落先民,当时是靠种植和捕鱼为生,而且生活资料很丰足。而这些陶片上刻出的奇怪符号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里的先民已经努力地创造自己的记事文字了。
半坡遗址彩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最先提议办个展览的是北大的学生,石兴邦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这可能是考古历史上最简单的一次“成果展”,现场就在那断崖下,文物就摆在桌子上,“很多人来看,一个月下来就有将近10万人”。
无意中,石兴邦和他的团队又完成了一次创举——允许群众入场参观,将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考古工作者为参观的民众讲解
这个“展览”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1956年陈毅副总理听了汇报后也特意到半坡遗址参观,当时石兴邦给他当讲解员,大家聊到半坡遗址的价值和成立博物馆的必要性时,得到了陈毅的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博物馆。
今天的半坡遗址博物馆
石兴邦曾说,如果再活一百年,他还做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
他也告诫新一代的考古人,每天和文物打交道,必须要身正心静,“我在北京那个贵妃墓和后来的法门寺地宫,那些金银财宝一抓一大把,这些东西古人又没有埋着账本,少几颗宝石谁会知道?我拿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那也不敢,连想都不想。我们只把它当成是文物,从来不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换钱的金银珠宝。不拿倒平安。我们要真正视黄金如粪土,不要留恋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英雄气概吧。”
03
今天,如果你去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会看到著名的昭陵六骏,但其中两骏并非原件——它们远在美国。昭陵六骏的毁坏和分离,令无数国人“意难平”,作为对国家历史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人,石兴邦曾差点促成两骏归国,这还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件事。
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可以说是古代帝王中最高,而且他自己还喜欢骑马冲锋陷阵,一线厮杀。李世民也是爱马的人,他在九峻山上修建昭陵时,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于是,在昭陵北侧祭坛的北司马门内,竖立起了六骏的石刻。据考证,六骏以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画作为蓝本雕刻完成。
这六匹李世民生前最爱的战马,分别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于1913年被盗,辗转于文物商之手,最后流失海外,后收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其余四骏也曾被打碎装箱,幸而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当初在西安一中读书时,石兴邦就听闻过昭陵六骏的故事,他可能比其他的人更希望昭陵六骏“团聚”。1986年,石兴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访美,与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交流时得知,张光直正试图说服当时宾州大学博物馆馆长戴逊,将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件藏品归还中国,戴逊那边已经表态愿意考虑。
于是,石兴邦也特意到费城去拜访了戴逊。在石兴邦后来的回忆中,他透露,戴逊本人也希望飒露紫和拳毛騧能回到中国,但这目前还是他个人的意见。戴逊还提到了两种可操作的方式,一种是交换,一种是借展,借展后再谈归还。这次交流中,戴逊很明确表示不要提过去的传闻(指被盗来的说法),因为他们博物馆是花了钱买来的。
石兴邦回到北京后,向夏鼐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访美情况时特别提到了二骏回归的事情,中方认为可以采取互赠的办法解决,即美方还赠中国二骏,中国回赠美方相应的两件文物为报馈。
可是好巧不巧,当时美国有一个教授考察团访问西安,在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昭陵四骏时,其中有位叫凯赛尔的教授是戴逊的挚友,看到了展品说明文字上有那两骏“被美帝国主义盜取,现藏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等字样。
凯赛尔回美国后给戴逊写了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信,信中说:“作为一个宾州人和一个宾州大学的校友,我想让你相信,我和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想到一所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尤其是美国这些意欲为其他国家作出道德上的典范的高等学府,展出着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展品,就异常难堪,感到很丢人!”“假如宾州大学果真拥有这两个唐马,假如我看到的说明属实的话,应该立即归还它的尊贵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假如中方的说明不符合史实的话,也希望能阻止这样的谴责。”
此信内容刺激了戴逊和校方,加上后来宾大博物馆人事变迁,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此事再无进展,也成为他的一件憾事。晚年的他,在纪念张光直的文章中,还依然表示,“我们仍在继续进行二骏回归工作”。
如今,这位百岁长者,已离我们而去。但先生对考古与文物的挚爱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编辑 段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