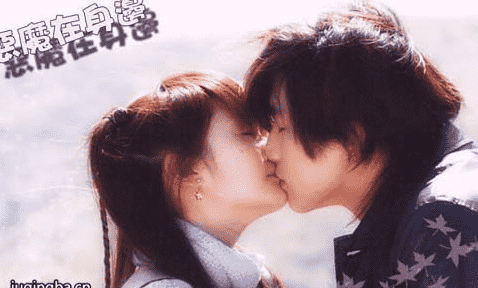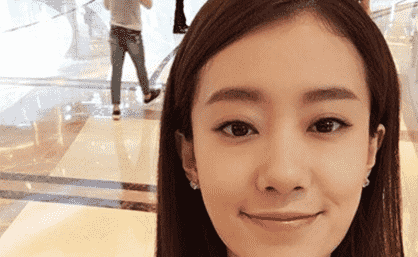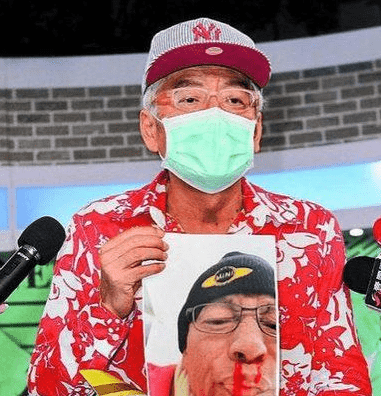【张惠妹演唱会】张惠妹演唱会 认为一直唱《听海》没意思

“大家常讲的乌托邦(UTOPIA),多半指的是英格兰社会学家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在1516年所写的《乌托邦》。书中虚构了一个大西洋上的小岛,岛上的国家拥有完美的社会、政治和法制体系。在这个国度中,只有几条法律规定,没有逞凶好斗的人,没有阶级差异,也没有族群的隔阂,人们用认真的工作来获得安乐平和的生活,他们以包容的心来迎接每个不一样。”《UTOPIA》巡演场刊以这个百科词条开头,使得我们对张惠妹用音乐构建的“乌托邦”产生好奇。推翻,再推翻,经历六年的磨合,张惠妹再次放出自己的“音乐分身”阿密特,新专辑《AMIT2》随之暴露于天下,“乌托邦”巡演的大门也道道开启。歌迷从听觉上认识张惠妹这么多年,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她心中的那片乌托邦更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除了阿密特自己以及经纪人陈镇川的解读,或许《偏执面》专辑最后一首歌《前进乌托邦》可以给出答案:“生活况味越简单越美,先跟烦恼背对背,拥抱无罪游戏不累,有爱什么都对。”
面对争议
怎么解读是你们的问题,我从不在意
媒体:从《AMIT》到《AMIT2》,阿密特让歌迷等了六年。为什么会这么久?
张惠妹:我做音乐都不太会管时间,最重要的是歌对不对,状况对不对,要表达的东西,我必须确定有十足的把握。时间过得很快,这六年中间,我们不断地在收阿密特的歌,并没有停。只是收了一些,突然觉得它们还不能够代表这个身份。我不断地在推翻,推翻,所以时间也就一直慢慢地往后推。倒是张惠妹的歌收得比较顺利,因此先有了《偏执面》。
媒体:所以《AMIT2》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酝酿过程?
张惠妹:我听音乐的感觉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如果拿出三年前收的歌曲,会发现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探讨的事情跟议题也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两年,我们收到了感觉很对的歌,也觉得是最适合我这个阶段的状态。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有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不太会去束缚自己,规避一些议题。因为阿密特,从出现的那一瞬间就是一个实验性性质的品牌。想要唱比较安全的作品,大家更能够接受的歌,还是交给张惠妹那个品牌吧,在那个地方可以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阿密特的品牌下,我必须要去做一些很大的改变,这十首歌我做到了自己的极致。对的时间点,对的人,对的样子,所以那就来吧。剩下的就让听歌的人去想,去给出自己的答案。
媒体:回头看2009年那一张《AMIT》,它不仅曾在第21届台湾金曲奖上赢得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女歌手等六项大奖的肯定,再听亦是一种经典。在这种期待下《AMIT2》出现时,视觉上冲击很大,歌词也非常犀利,引发了一些争议。想听听阿密特的这次突破是怎么产生的?
张惠妹:大家都知道,我很不喜欢去做这样的事,如果我有意要做有争议点的东西,可能在这十几二十年,每一次都会去做。所以《AMIT2》的这些争议点并非是我要去做的一些预设的立场,那不是我的本意。我们当初在收歌的时候,它们完全不是现在长成的这个样子。先有了曲子,我们才去研究歌词,去想要表达什么。录制完歌曲之后,才会有视觉。视觉的部分,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去表达我所要说的一些话,磨合了许多。这个部分对于导演,以及参与视觉工程的人员来讲,他们花了时间,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其实,当视觉画面出来之后,说实在的,我自己看了也会觉得是不是太惊悚。但是它刚好可以呈现,我每首歌都有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媒体:所以面对已有的争议,你是怎么看待的?
张惠妹:我其实完全不会去在意那些。因为这些成品,都是经过我们全部人的讨论,觉得它是对的,最后才出现在大家面前。不管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我觉得你绝对不能够、也没办法让十个人里每一个都喜欢。十个人里,出现喜欢与不喜欢的冲突,他们讨论的点是什么,这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因为音乐是很自我的,这六年期间,我所有想说、想看、想表达的,都在这张专辑里面。如果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我觉得那个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有任何的担心,或者是不开心,我觉得很好,非常好。
不唱金曲
重复自我容易,但这对不起自己
媒体:这一次“乌托邦”巡演的歌单有点特别,我们可以预期的金曲被折叠,这种想法是怎么成立并且实现的?
张惠妹:这应该是个性使然。就这次的演唱会,我们前期做了两三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一起工作的团队都觉得之前“Ameizing”那一轮巡演是非常成功的,用那些歌曲,张惠妹的,作为一个十五周年的总结,所有人都很喜欢。然后,当我们在讨论这次乌托邦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的模式完全跟“Ameizing”一样,我就觉得不太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挑战性。我真的可以永远唱《听海》《剪爱》,我相信我的歌迷,在经过每一次不同的编曲,不同的视觉呈现,他们都会接受。只是对我来说,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尽量说服我旁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把歌曲全部排出来,我就拿笔开始划。划后,他们说“这位小姐,你把所有可以唱的歌全部都划掉了,那你要唱什么?”我说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有一个能挑战自己,也可以挑战歌迷极限的演唱会。因为演唱会不是天天都有,要准备一个演唱会,也许要三年、四年、五年。如果我一直在重复做自己,当然非常有把握,轻而易举,但我会觉得对不起我自己。还好工作伙伴体谅我,他们绞尽脑汁,帮我开出一个歌单,把它拼凑成一个所谓挑战我歌迷的演唱会。之前台北的十场,其实是我最忐忑不安的十场,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表演方式。大多数演唱会,都是顺理成章,先从轻快,到慢慢堆积,到热情,最后到“辣”,这是一个略常规的路线。那,我就把它推翻。我刚开始就下重的,一个半小时的阿密特演唱会,我把所有的新歌都放在里面。他们也曾对我讲,“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子的演唱会,现场的歌迷如果不买单,就必须要有心理调整”。我觉得这是我的挑战,而且我对歌迷也很有信心,他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新鲜。所以那十场之前,我是很忐忑的,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首唱完后,我信心就开始来了。第八场的时候险些到了极限,以为没办法完成十场,但还是撑过来,我在后台给自己掌声。

《怪胎秀》
《怪胎秀》这首歌录音的过程很过瘾。编曲、和声、各种磨合,也唱得很HIGH。录了很多次,每一次都不一样,也在不断地超越预先设定的高点。而它也是第一个被大家所讨论的。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在讨论它有多怪异,或者是说马戏团有多厉害,我们只想表达的是“很多时候人在看别人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很沉静、有意见的眼光去看,但是从没有想过别人怎么看你,或者其实你也是那种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醒思,我们怎么看待他人,也许人家就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斟酌你所谓同意跟不同意的时候,你必须稍微留点情面。
《战之祭》
老鹰在我们卑南族的认知里是正面的,力量的象征。这个图腾与阿密特这一次想传递的东西是一致的。在录音时进行到《战之祭》,我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覆盖,甚至拉动极限,飙出了自己极限之外的高音。后来视觉上,导演比尔贾把我包装成鹰之女神。拍摄过程中,他一度捕捉到我鹰一般的眼神,甚至兴奋地喊出“我抓到了!阿密特!我抓到了!”。我自己看到时也是热泪盈眶,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做到这一步。
自述
A-mei & Amit
A-mei 听到她会有共鸣,适合疗伤
Amit 她是阴暗面的我,甚具争议
对于张惠妹,大家认识我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出道时十八岁,大家对阿妹这个身份已经有了一个很既定、鲜明的印象。阿妹是最适合唱情歌的,她是最适合疗伤的,她是最适合唱一些性感、轻快的舞曲的。总之她传递出来的东西是正面的,疗伤的,听到会有共鸣的,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生活里的个性。而阿密特音乐的部分,我一直说它是实验性质的。音乐是可以玩出不同的东西的,只是说你在玩不同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造出另一面,这个也可以是你自己。而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去假装是她,那就不成立了。阿密特,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她属于我比较阴暗的另一面,也是我,只是不轻易表现出来。只有在最私密,我心情最低落、发生起伏的时候,阿密特才会出现。她可能是大胆的、直接的、前卫的,甚至有争议的,但我希望可以用这个身份,没有任何束缚地去表达。
在舞台上表演,张惠妹与阿密特,我并没有刻意要去分开她们。只是当音乐前奏起来时,阿密特的音乐一出现,歌词一跟进,我就会自然地进入到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很巧妙,也很高兴,我可以尽情地在舞台上享受这个转换式的表演,而不是虚假的,去扮演。两种都是真实的,很过瘾。——张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