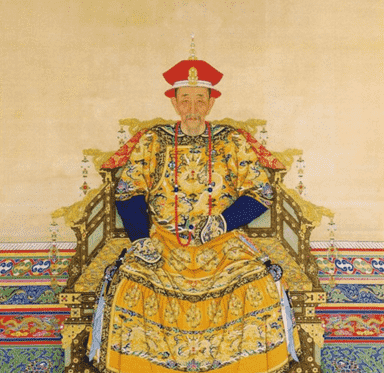“船户”陈瑶、赵丙祥:“江湖”中的船民、船歌与大历史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澎湃新闻的《陈瑶、赵丙祥:“江湖”中的船民、船歌与大历史》,希望大家喜欢。

《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以下简称《江河行地》)是商务印书馆“日新文库”推出的新书,作者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瑶。近日,本书作者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赵丙祥一起在京进行新书座谈会,座谈由《江河行地》一书责编齐群主持。本文整理自座谈文字稿。经发言人审定。
齐群:我是《江河行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学习经历横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专业,看到陈瑶老师这本社会史研究感到格外的亲切。本书前半部分很多分析性的内容,包括长江船户的基本状况,近代以来的长江中游船户的生产、组织,如何应对国家的差役,等等,这些都非常精彩。但最触动我的是,陈瑶老师在结语里和一本社会学比较熟知的文献对话,这就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老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同样都是广义的交通产业的从业者,又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的“边缘群体”,在明清民国和当下都有着大不相同却又十分相似的遭遇。
陈老师的上一本著作是《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那么您是怎么从米业研究转向到船民研究的呢?
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研究米谷贸易的时候,因为运输米粮需要非常多的船户,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史料,所以对这个行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湖南的湘乡县一个船户的家族族谱,就开始了这项新的研究,希望能从整个长江中游流域寻找更多的更广泛的资料来讨论这个行业,以及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讨论传统行业从清代到近代以来的转型历程。
在研究过程中,我非常幸运地搜集到很多关于船户群体自己创造的文献,包括水路歌、船歌号子,还有他们自己记的账簿、签的合同、家族的族谱、碑刻。另外我还去档案馆找到大量的民船业档案,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外学者调查报告。
这些丰富而多元的资料,让我眼界大开。我本来以为船民是底层群体,可能遗留的资料极少,没想到能找到这么丰富的文献,而且是来自不同立场、不同群体的声音,这让我们知道社会不只是一种声音,我们可以从更丰富的资料去看到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的现实状况。
在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有时候非常感动,特别是看到抗战时期的民船航运业的船民是怎样去组织,既保留了传统的船帮组织,也有民国时期新产生的民船行业组织。特别是在湖南,大家知道抗战后期,湘北的战场是非常惨烈的,公路、铁路、轮船,这些现代交通方式基本破坏殆尽了,这样的情况下,长江中游的传统民船航运实际担负起了前线军需民用的运输工作。
1920年代初汉口江汉关及码头繁忙景象,陈瑶供图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员、船只和财产,损失特别巨大。传统史书里面,通常把船民这样流动性很高的人群称为“江湖匪盗”,这是很带有歧视性的蔑称。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这个群体得到政府公开的认可和赞许。这样的变化的过程让我非常感慨。
在研究船户和木帆船航运业的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其实有现实的关照,比如刚才讲到的大卡车司机这个群体。这些流动性的劳工群体,他们的流动性为什么会让社会大众,包括官方、读书人,甚至是商人,会有一种不安感?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不安感?
通过这个研究,我觉得虽然船民是流动性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也非常依赖整个市场,政府的疏导管制,甚至是科技的进步,都能让社会大众逐渐地接受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群体开拓出来的新的空间,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网络购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一下子进入这样一个新的空间,但是慢慢地,大家都接受了,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购物。
之前一些宣传,有用到“社会边缘”这个词,我在书中尽量没有用这个词,我相信船民并不是边缘,他们就是中心,起码在我的研究里面是一个中心,在我的生活里面也是一个中心。我并不是用单一视角去看待我的研究对象,恰恰相反,我在田野中收集的多元材料向我展示了这样一个群体自在的生活,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某个所谓中心的边缘,我在书里也努力想把这样的视角传递给读者。
我特别感谢我的历史田野受访对象。我去湘乡的船户家族进行田野考察的时候,他们对我特别好,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料,他们让我了解到,这种流动性很高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人,其实跟我们和在座各位都一样,都在追求一种很平安、稳定、积极向上的生活,并不是像传统的主流历史文献里面所讲的,都是一些“江湖匪盗”,给社会带来不安的人群。
齐群:之前在谈起中国社会的时候,赵老师经常强调钱穆先生一个重要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类,就是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陈瑶老师这本书研究的人群和历史场景,可以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江湖”,因为船民和帆船只能在江湖上运转。您的研究比较关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乡村里的宗族,城镇里的武艺群体,这些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比较紧密。但是陈瑶老师这本书,却把一个距离我们稳定的日常生活比较远的社会系统给呈现了出来。您怎么看待中国历史中“江湖”这个社会系统,以及陈老师笔下这样一个漂泊不羁的船民群体?
赵丙祥:这本书我看得比较仓促,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陈瑶老师再批评。
齐老师说船民离我们比较远,这可能是北方人的经验,如果我们到南方去,我们看费老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乡村经济》,过了淮河以南,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船恰恰是人们生活中最关键的东西。在传统时代,北方平原多,交通多骑马,南方河流湖泊多,交通多坐船,所谓“南船北马”就是指这个。还有,关于船民群体,我比较同意陈老师的看法,现在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是“边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到底谁才不是边缘呢?
另外,这本书为什么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全书涉及整个长江中游流域,但重心是湖南,最出彩的还是跟陈老师的老家湘潭有关系,从书里能看出来,她收集材料、田野的体验,历史现场感特别好。
长江中游流域示意地图,陈瑶供图
那么湖南这个地方为什么比较特殊?对我们来说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近代更早的时间,这里诞生了湘军,湘军对于理解整个晚清历史,一直到近代历次革命,都非常重要。第二,中国革命,湖南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人物,特别是这本书研究的涟水流域,湘乡、湘潭,就有毛泽东、刘少奇等很多革命领袖。理解中国革命,离不开湖南,特别是湘潭这样的地方社会。第三,在抗战时期,陈老师提到,北方和江南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前三次长沙会战,整个湘江流域船民船帮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回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阶段就会知道,为什么长江中游那么重要。它不仅是长江上、中、下游三种地域社会类型的中间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域有它的特殊性。学术研究中,我们当然会认为每个地域都有它独特的研究价值,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对特定历史阶段来说,不同的地域社会,它的研究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湖湘这个地区,尤其是湘潭这个地方,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一直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都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
说到湖南,我们会想到什么?今天的湖南想象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浪漫的,如果我们是文学爱好者,会想起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这篇小说我们真读进去会发现,它背后藏着另一个社会,这里虽然谈的是湘西,但是对湖南甚至对整个长江中游都是有代表性的。沈从文的《边城》中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惨痛的历史,当然了,沈从文先生写得很是隐约其辞。老大天宝驾船离家,死在外边了,老二傩送也走了。这就是湖南的另外一种历史的现实的想象,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水乡的生计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霸蛮的江湖土匪社会。我们小时候热播的好几部《剿匪记》正是这种反映。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江湖”当然不可或缺,在今天一般人说“江湖”往往是贬义的,学术界倒不一定这么看。钱穆先生说得特别对,认为江湖是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放在今天的学术话语里面来研究、写作,陈瑶老师这本书我觉得特别感动我的是,她在这方面的关怀比较大。
这种关怀可以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这本书的开篇,就会知道陈瑶老师的研究继承了华南学派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说总体上要关注整个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但要从地方社会入手。但是地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做一个地方不顾及其他。中国近代的历史,沃勒斯坦意义的“世界体系”扩展到东亚之后,从五口通商开始,整个中国面临着巨大冲击。以往学界的解释模型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外国冲击来了,中国受到刺激后要回应;另外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即“帝国主义”模式,中国的转型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同步展开,这两种解释其实在底层逻辑上还是有一些共通性的。
这些解释当然都有道理,但是也潜藏着问题,这就是陈老师在开篇提出的,如果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长江中游的传统木帆船应该马上被现代轮船取代,但是她发现其实没有。刚才讲的中国近代几个历史阶段来说,传统木帆船航运业的船民和船帮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轮船这样一种现代运输工具的到来,反而在一定的时间内,促成了长江中游水系中交通方式的多样化,现代轮船运输与传统木帆船运输是共生的,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取代关系。这个研究其实背后有一种世界史的关怀。
不论是世界体系扩张,还是现代化转型,我们在今天或多或少有一种担忧,那就是地方性的东西会不会消失。读完陈瑶老师这本书后我们发现,尽管书中没有直接涉及当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感受到,这种地方社会的多样性,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更可能是转化了。所以通过船帮的研究,我们看到这些船户的生活,他们的宗族,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第二个方面,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很愉快的阅读体验,读到最后甚至有一点忧伤。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让我很感动,书中用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就是水路歌。船工出航拉纤,到过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行船危险,他们就把到过的每一条河、每一个渡口、每一座城镇,滩头、大山,都编成歌谣唱出来。我们知道这些船工很多是独身的,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是单身汉,他们去世的时候,他的亲族或者同行工友,会在他的葬礼上唱水路歌。中国人有一个习俗,临终之前要在身上盖一床被子——清代皇室成员死了要盖陀罗尼经被,普通人只能盖一床完整的被子。而这些船户在去世的时候,他的同伴们会在葬礼上给逝者唱一首歌谣给他送行,就是“水路歌”。陈老师用的词叫“生命地图”,这个特别好,在船民一辈子将要终结,结束在这个世界的生命的时候,也会给他盖上一床被子,水路歌里的那幅地图就是这床被子,把他驾船走过的每个滩,每个渡口,像一床被子一样盖在他的身上。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热闹的葬礼上,那些船户唱着水路歌,一起送他们的同伴踏上黄泉路,有一种东西是很悲凉的,其实也是唱给自己的啊。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盖棺定论,而是给一个光棍汉一辈子的总结,真的特别感动。
在这个方面,我自己从华南学派也学到很多,他们的历史人类学,对田野现场感的强调,我觉得是这本书特别出彩的地方。前面说到我为什么不同意用“边缘”来描述船民群体,因为这个词确实有点问题。刚才提到的生命地图,恰恰是一种多样性和生命感,是船民自己的人生。
第三个方面,我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人类学,这本书对社会学的启发是什么?书的结尾处引用了沈原老师的中国卡车司机的研究,今天湘江上面已经没有这么多船了,但是我想陈瑶老师想告诉我们的是,哪怕很多人不再坐船了,但是在中国的无数条交通动脉上,公路、水路,其实还是有同样的人群。在这点上,历史学家强调这种田野现场感,去实地考察,反过来,对社会学家而言,我们今天做研究的时候,要从他们那儿学会怎样进入一些真正的历史感,一个完全没有历史感的社会学研究,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生命力的。
齐群:在赵老师的评述中,能感受到我们经常讲的“文史不分家”,我们能够在民间文献读到一种非常真挚的情感,这个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活灵活现地真实存在过。
刚刚赵老师谈到了第二部分,强调这部分引用了非常多元的文献。实际除了最后一章讨论水路歌之外,这本书还有专门章节分析船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引用了大量的船民日常账本。这本书直观地展示了陈瑶老师的文献收集和分析能力。我想很多读者对于历史学者的日常工作了解比较少,那么,请陈老师给大家展开谈一下,您如何从发现了一个家谱扩展到整部书的研究?
陈瑶: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讲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我最大的感触是,做历史研究,去田野,运气非常重要。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宅”,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在家看犹他家谱学会公布的湖南的一些族谱,我在那儿翻目录,发现湘乡的白沙陈氏族谱,里面有一篇《河埠记》,就讲他们怎么管理河边的码头,我就想,这个码头归他们管吗?于是查询了这个家族在哪个地方,过完年我找时间就去了。
到了湘乡后,我的运气非常好,当时刚好有一个从这个家族走出去的人回家寻根,他就想找自己家族的历史。当地的族亲非常热情,给他看族谱,带他找碑刻,寻找祖上的坟墓。以前的石碑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受重视,有些就拿去田埂上搭桥了,因为碑的石材很好。好在搭桥的时候,石碑的字是向下的,没有被踩踏磨损,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乾隆年间的碑文,还有一块是道光年间的碑。这些碑非常精彩地记述了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管理码头的,怎么样垄断这条河流的运输权的。
还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回去寻亲了之后,白沙陈氏要重修族谱了,他们就把以前的族谱都找出来,还得去各地查访,从这个家族分散出去的分支。陈氏的人都特别好,在这个过程中搜集到的族谱,全部做成电子版发给我。还有两位老人家,80多岁了,会唱水路歌,当场唱给我听。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进入到了历史之中。他们两个人唱完之后跟我说,你运气很好,你再要听到这个水路歌,只有一次机会了,虽然我们还有两个人,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了,我们两个看谁先去世,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就没有人再给他唱水路歌了。
陈新开老爷子,家里现在还是家徒四壁,但是他说他过得很好,他现在能领退休工资。我的书里也写到,涟水的船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转型成了国营企业,所以他成为一个企业职工,不是一个农民了,有职工退休工资。这些老人的生命故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就寻着水路歌,走上了一条新线索。
湘潭县档案馆也非常好,从我读本科开始,就一直非常支持我,我去查询档案,都能调出来供我阅览。他们有比较丰富的民国档案,抗战时期湘潭沦陷的时间非常短,只有几个月,不到一年。他们在沦陷之前,就把其中的大多数重要的档案,用船运到乡下,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批民国档案。这里面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抗战时期他们是怎么样组织民船的团体,如何延续着原来船帮的组织,怎么样跟汉口的船帮组织连接,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如何在抗战的过程中维护运输的秩序,来实现军需民用的运输的工作。
《无名氏船户1934江河总簿》之一页,陈瑶供图
这些一个一个的线索,会慢慢地引导你去寻找这个社会群体留下来的声音,在档案里面就有他们的账簿。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一般以为这些船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可能不怎么会写字,也可能不会计账,但是没想到,在1934—1953年间有大概9种账簿留存下来,是他们手写的。这里面是一个一个的人,他们的名字,后面记他们的工。比如今天到这个船上,给船老板打了一天的工,他就画一个圈,打了半天工,画一个圈加一个横。我慢慢地学习、认识这些符号,慢慢解读这些文献,逐渐地分析出他们打一天工能赚多少钱,再跟其他的行业比较,就会知道他们的工资水平其实不算低。但是他们不稳定,就好像现在的卡车司机、快递小哥一样,虽然有时候能赚到很多,但是长时间算起来,是一个不稳定的劳动的生计模式。
上面这些丰富的资料,是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多元的资料会呈现出多元的声音,不会让我们沉浸在一种声音里面去理解这个社会。我还是比较喜欢或者比较倾向于在历史研究里面,尽量多地去搜集研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去理解它。这些历史记录有时候会互相矛盾,互相冲突。我们在官方的档案里面会看到,这些船户经常偷扒、盗窃,甚至把商客推到河里面去,抢劫他们的财物,档案里有非常多的刑案卷宗是在讲这些故事。如果单单从官方的记载去认识船民群体,你会觉得这些人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大多数船民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这个高度流动的劳动群体,其实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平安稳定的生活,没有人想做一个匪帮首领,成天被官府缉拿。所以还是需要多元的史料来呈现多元的声音,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体的面貌。
《湘潭船行成案稿》之一页,陈瑶供图
齐群:开展历史研究最关键是能够扎实地找到活在当下的多元历史材料,的确像刚才陈老师提到的,能够在历史田野中遇到一个还能唱水路歌的老先生,的确会给研究者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熟悉的历史研究,往往是政治史的研究,大家觉得中国传统史籍特别是传世文献,会有确凿的历史,研究者通过不同的史料的对勘和训诂,尝试把历史的真相挖掘出来。但是我在编辑陈老师的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多元的民间材料,有时候呈现的图景并不是和现实那么严丝合缝。比如我们看水路歌歌词,感觉到船工一下去了上海,下一站就跑到扬州去了,一会儿又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他的前半程可能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后半程只是稀疏的大码头、大城市,这个时候会给历史研究者提出很大的挑战。因为这种史料并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是非常严格的档案或者传世文献,民间文献的解读会有更多的奥妙。
赵老师特别强调水路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地图,是一个生命的地图,那么您能不能在这方面向观众和读者展示这样非传统的文献怎么解读,以及什么意义上水路歌是一个生命的地图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地图呢?
赵丙祥:我读这本书到最后的时候,也多少有一点困惑,陈老师的解释,在我看来多多少少有一点矛盾。第一,水路歌的内容特别丰富,之前在聊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希望陈瑶之后还能再出一篇文章,把水路歌的意义更充分地展示出来。因为水路歌里面的记载,绝对不只是河流,中国人经常讲山水、山川,水和山一定是搭配出现的,这个传统太久远了,从《禹贡》开始就是这个模式,到现在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水路歌的叙事逻辑是,一个船户想象他驾船在一条河上航行,经过哪些个滩头,但接下来一定会有山,同时还会有人住的地方,比如会唱到了哪个城镇,有一些繁华城市还更远,比如扬州,在远离湘乡的长江最下游。
怎么理解水路歌的歌词,陈老师的解释是,水路歌有非常实用性的一面,她有一个参照,中国航海史上有一种文献叫水路簿,尤其在东南沿海到南洋这些地方,比如从泉州出发,多少里路程会有什么标志,可以在这儿歇脚,再有哪个地方风大浪急,要特别注意。水路簿和水路歌有这样实用的性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又觉得,似乎不能完全用实用性来解释内河的水路歌。河道水运当然很凶险,但是它跟海运的性质还是有差别。这个差别是什么?陈老师的词用得特别好,为什么叫“生命地图”,有些地方显然是船户没到过的,甚至很多船户终生只跑小段固定航程,比如一辈子只跑涟水到湘江这段航路,快到长沙的地方就不继续跑了。但这同样不妨碍船户会唱更长段的水路歌,比如湘水下游甚至一直到长江下游的歌。这个现象怎么解释,这本书在这方面稍微有一点点不足,我特别期望看到陈瑶再写这样一篇更深入研究的文章。
我们毫不否认水路歌这类民间文献有实用性的一面,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它有自己的想象世界,所以在水路歌里出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船户也有家室,但确实也有很多是没有成家的。船户的水路歌里有不少爱情歌,他是用唱民歌的方式去想象一场爱情的生活,那里面与岸上女性的情歌对答大概率不是真实地发生过的,他会唱,到哪个滩头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还要招呼妹子跟他走一遭,这其实是他们想象的场景。女船户很少很少,大部分从业者是男性。其实这是他在想象,自己成不了婚,或者远离了家,是对所缺乏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一个想象。
这种想象不限于个人的家庭和情感。比如说,一个船户没到过扬州,那么去过扬州的人说扬州是什么,扬州就像是十里洋场,那个地方有好喝的美酒,有好吃的美食,有好看的风景,还有漂亮的姑娘,船户可以唱出来的。也许一个船户这一辈子可能只在涟水这条支流上讨生活,但他的世界不会被涟水限制住,他的想象可以一直通向扬州。
这个想象世界跟前面呈现的现实世界,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地图”。第一层,陈老师的这个研究,在世界体系、国家总体经济运转的现实背景里,看一个地方社会和一群人怎么生活,这是一个现实地图,可以根据资料的客观记载勾勒出来。第二层,这本书用到了账簿、家谱,这些和他们日常的生活、社会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一个社会网络地图。第三层地图,就是船户把自己祖先视作神明,我记得她写了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大族,一部分族人明明已经不在河边,迁移到内陆甚至深山里挖矿去了,但他们拜的祖先仍然可以是水神,两者之间有错位,水路歌反映出这个世界,它的第一层、第二层是不完全重合的,但是有交错的关系。
江西赣州储君庙中崇祀的滩神,陈瑶供图
这就展示出来,其实船户的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一方面在近代这个时段内他们处在一个大的世界进程里,也是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地方又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而这样一个生活世界又不妨碍他们有自己想象的非常大的世界。为什么我一直喜欢华南学派的研究,他们也做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做仪式的研究。我们的老师一辈写过很多东西,他们研究的时候一定不脱离社会经济史,这个特点特别值得当下的社会学、人类学虚心学习,我们不能一说仪式、文学,马上全是主观的想象,全是象征的、认同的研究,这很容易造成一个研究漂在外面,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文学,不管是文人的还是民众的,与所谓现实的关系比这个复杂多了,在“实在”的意义上,哪会是那么简单,不是反映论能解决的。
刚才提到了三层地图,甚至可能不止三层,船户们的世界是多层次的,有大的,有小的,互相叠加,但是又互相不能够完全涵盖。将这种复杂性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研究。
齐群:感谢赵老师的深入分析和评议,让我们打开了新的世界,作为普通读者或者非专业的研究者,阅读到这本书或者其他相似的社会史的研究的时候,很难区分出这么多层级的世界。很多人的第一直觉是,会有一个很现实的世界或者历史,但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一个想象中的生活世界,往往需要研究者、阅读者的共情能力才能去理解、体会。
(蒋荣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