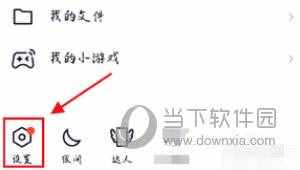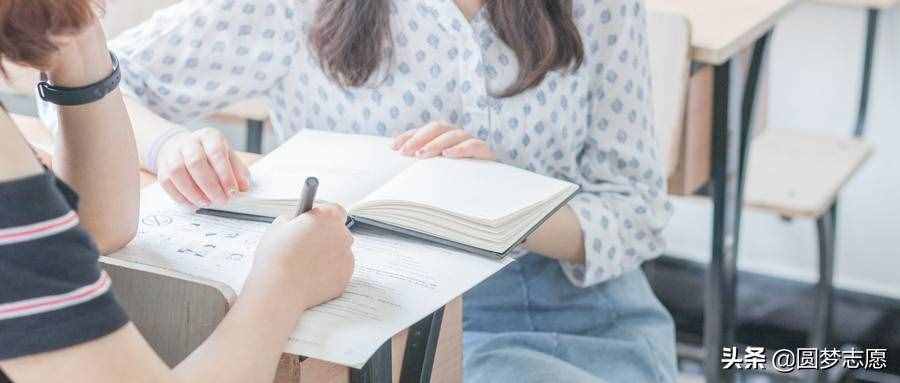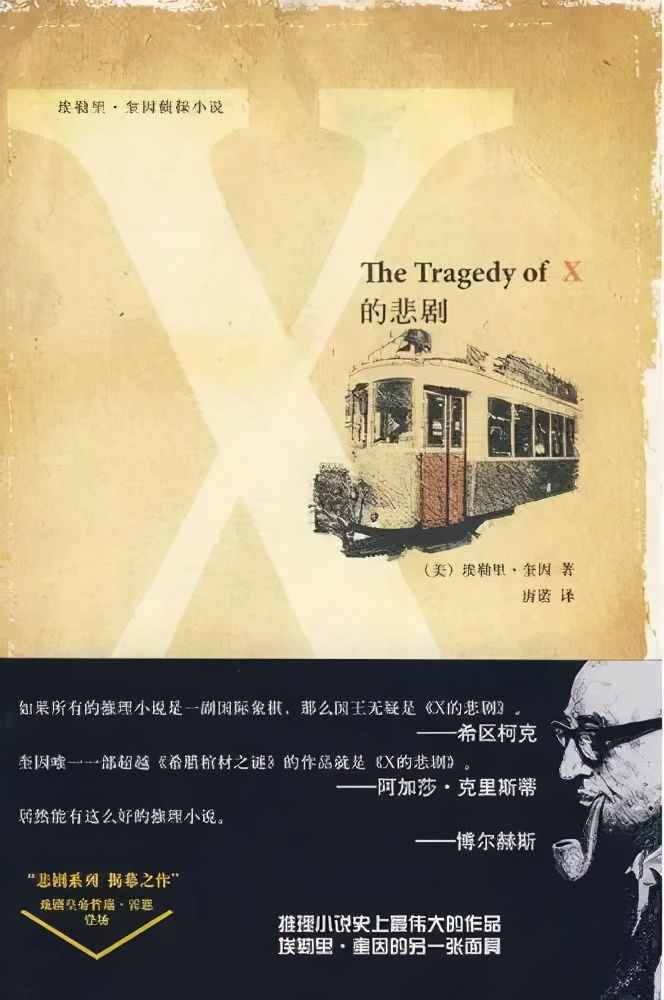“回民”左宗棠为何要把陕西回民西迁?真实原因:看关中汉回仇恨有多深?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惊艳时光的哲学的《左宗棠为何要把陕西回民西迁?真实原因:看关中汉回仇恨有多深?》,希望大家喜欢。

左宗棠为何要把陕西回民西迁?真实原因:看关中汉回仇恨有多深?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官府分而治之、分隔治理的思想在平定回民起义中早已表现出来。
其中同治元年清军规复陕西,朝廷上谕“将王阁村等处巢穴悉数扫荡,务令拔其根株,以渐解散。”
在此授权下,对聚集于王阁村、羌白镇、仓头、渭城湾等处回民进行极其残酷的镇乱和驱离,导致这一阶段军事行动之后,陕西关中(除西安城内)再无回民居住。
同治十三年(1874),平定肃州后,清军亦实行了大规模的有目的性的大屠杀和迁移行动,使河西走廊2000余里基本再无回族居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隔绝关内外穆斯林的统治目的。这两起事件都是经由朝廷的上谕、军政大员的命令公开实施的,是一种典型的分隔族类的政治考量。
其他各起繁多的屠回事件在以往的回民起义史研究中被予以过度的定性,但其实大多数的此类事件只是分散的、民间的、或半官方的行为而已。
对于陕西回民来说,清末以国家军事力量平定回民起义,实质上一直持续着将他们自家园“驱离”的过程。
1、关中汉绅阶层的仇恨
在镇乱之后,官方采取了一系列的迁徙、禁教、强制教化等善后措施,将他们与原来的汉族邻居分隔开来,与甘肃回民分隔开来,使他们再也没有重新回到原来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汉绅的意见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民起义使陕西的广大乡野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摧残,而城镇则基本得以保全,汉绅阶层基本集中于城镇之中,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
士绅向来是清朝朝廷处理地区事务的顾问,在回民起义期间,国家军队要依赖他们解决相当一部分粮饷和地方治安,他们对国家机器的影响力因之大大增加。他们积极介入清军和官府的决策,对今日西北回汉分布的格局施加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军开始平定起义回民之后,所谓“在汉民之心,欲借朝廷兵力尽灭回人,即快私仇,又除后患”。
汉绅们积极游说清军加强对回民军的攻势。
他们的诸多言论毫无顾忌地表达他们的民族仇恨或“种族主义偏见”,如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末,多隆阿进攻起义回民据点王阁村时,回军遣被裹挟的前清回民将领哈连升求抚:
“时人情汹汹”,以县举人张逢午为代表的汉绅纷纷具禀反对抚局,谓“回性叵测,狡诈非常,图远交以近攻,每朝盟而夕改,自始祸至今,变诈百出…今虽屡挫凶锋,然尚非倾巢覆穴大加惩创,则未必贴然心服。且闻该逆勾结外援力图抗拒,窥其乞抚之辞,实为缓兵之计。”
言下之意,无非希望清军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起义回民。
甘肃战争阶段,汉绅仍然继续在发挥着他们的影响。
贺瑞麟,陕西三原人,是当地汉绅,学古、正谊书院的主讲者,关中理学的大家。
这样的人物,自然深深秉承夷夏观念,成为华夷之辩、驱逐回民的积极鼓吹者。 他的家乡于同治元年五月被回民军攻毁,创钜痛深之余,屡次上书大员,既坚决反对抚局,也坚决反对将受抚回民重新安置陕西。
在《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中:
一则言回性狡猾,降是伪降,投是假投,不可相信。“夫逆回豺狼之性,狡谲百端…则今日之投诚,安可遽保无他。”
二则言回民杀官屠城,当有剿无抚,以绝后患。“今逆回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惟有君臣上下,始终一心,有进无退,有剿无抚。”
三则言汉人被害特深,仇恨填胸,“谁肯与之共国而处,比屋而居,方将共图报复,以快一朝之愤。”
回民的报复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和社会残破,官绅亲眼所见,自然成其借口。
四则言“叛产”已经招种,屋宇自行焚毁,“纵使可归,正难安插”。
五则故耸其辞,言西安搜出铜器械等物,众回将举马百龄造反。“逆回若归,内外勾结,事益难料。”
总之,他的意见是“是即杂处甘省州县汉民之中,亦无不可,而陕西则万万无可容留之理。”贺瑞麟出于刻骨仇恨,故发激烈之言。
但是类似的意见对主政官员产生了有效的影响。
接替刘蓉任陕西巡抚的乔松年最初“亦有招抚陕回之意”,但最终他的意见是“陕民一闻抚回之语,痛心疾首,非文告口舌所能挽回,回民之屋宇为汉民所毁,坟墓为汉民所平,回民之田亦悉为汉民所有。其势两不相容,断难杂处,安插之法,除已抚甘回本系土著,其陕回必须于北山一带择空旷之地可以开垦者,计亩授田,资以牛种,课以农耕,编以保甲,方可冀其相安无事。”
当时其他官绅,均大体一致的认为进行善后,必须将回汉区隔开来,双方势不能居于一处。
官绅这样的共同经验又均来自于对发(太平军)、捻、回的不同认识。
地方士绅李启讷指出:
“况捻匪、发逆如果投诚,即为良善汉民。回匪投诚,仍是当日回民,即使王法宽宥,若与汉民相处,依然视为异类,臭味不投,积怨难释,此回匪甘受诛戮而不辞也。”
陕西按察使张集馨也认为:
“发逆与回逆不同,发逆本系良民,一经改悔,各有籍贯可归,或编入营伍;回逆本系异类,不读孔孟之遗书,不知国家之正朔,自成一教,与汉民冰炭不相能。”
后来主政陕甘的左宗棠也有类似的观念:
“回患与发捻异,长发薙头,捻贼弃马械即与常人无异,故战胜后即可解散安抚,以速戎机;回则习俗既殊,形貌又别于汉民,与之构衅既深,见则必杀,良回虑解后无策自全,匪回则以此劫持其党,得以自固。”
从士绅到官员,都一致认为起义回民与太平军、捻军有着基于族类的重大差异,这种认识支配了他们后来办理善后的政策方针。
2、左宗棠的选择——汉回分置
左宗棠在多篇文牍里都明言“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这种比较客观的认识,使他对汉绅的意见有比较审慎的考虑。屡有汉绅上仇回、驱回、杀回之禀,他便作出如下批评:
“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尽杀’乃止,併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
他对汉绅一意主剿的意见心知肚明,却非常不赞同:
“惟秦人议论,往往不可尽据。即如汉回争哄,致成浩劫。力主剿洗,万口一声,生心害政,实由吠影吠声致然,虽贤知之士,亦有不免。非兼听并观,折衷至是,不能平其政,祛其弊也。”
在这样的结论前提下,当平凉公局绅耆韩尚德等禀请将投诚回民安插远方,以示畏儆时,左宗棠便痛批:
“原禀称须安插远方,以示畏儆,不思回民籍本陕甘,陕甘汉民不能与之相安,远方之民独相安无事乎?…自古驭夷之道,服则怀之,贰则讨之。即内地兵事,剿与抚亦断无偏废之理,何得异议横生,以势不两立等语居然冒渎。”
但不管怎么说,左宗棠为抚局及善后划定了基本原则,其实质仍然是将传统非我族类的夷夏之防,运用在治回政策中。
他的策略其实与绅耆们的意见并无区别。
在善后重新安置回民的计划中,为了免除以后再发生回汉冲突的后顾之忧,左宗棠就有意将回、汉分地安置。
实际上,善后安置的绝大部分回民是陕西回民,则安置的首要原则便是不准回归原籍,而是另觅他处:
“回之求抚虽属实情,但陕回与汉民仇隙既深,自无准其回籍之理。计惟于近陕之甘境,或陕省北山一带,徙汉置回,方可以规久远。”
在这种思考下,他将目光转向平凉府境内:
“爰度其地于平凉得化平川广轮百有余里,泉甘而土肥。…既而河狄西宁肃州以次平定,肆赦之陕回既众,化平之壤地难容,乃分插平凉之大汊河、华亭之十二堡、秦安之龙山镇。既而复患人满,始散寄静宁隆德之间。”
上述这些地方多为山大沟深之地,共同的特点是“汉、回无仇,汉民较少,荒地较多”,其他陕西回民迁居的平凉谢家庄、姚家庄、张家庄、曹家庄,会宁姚王家,曲家口,静宁州隆德县王家下堡、刘戴家山,安定刘家沟、石家坪、好地掌等处无一不是“水草不乏、川原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后日都成受抚陕西回民最主要的安置地。
左宗棠将陕西回民远置,毫不掩饰他分隔汉、回的意图,“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
3、陕西回民西迁
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他的目的是维护清廷的统治,因此他明确地强调此举“暗寓徙戎之意,方可以规久远而免后患。”
这也表明经过十余年的乱斗,回民在清代官员文人主持的政治文化架构里,其定位与处境并无丝毫改变。
左宗棠办理善后,在把汉、回分隔开来的同时,也注意把回民分别安置。
如同他认识到动乱期间各地回民的区隔,他也认识到回民内部的差异与矛盾是善后必须要考虑的。
他说:
“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隶陕西者,有籍隶甘肃者,当其并力抗拒官军,固无分彼此之分也,一旦缴马模就抚,还为齐民,则甫被新恩,旋寻旧怨,不但陕回与甘回气类攸分,即陕回与陕回、甘回与甘回,亦有不能并域而居者。”
实际上,上述被安置于平凉府属各地的陕西回民,本就是被作为应该迁移的“客回”而从灵州、西宁等地甘肃回民聚居地区押送安置的。
如西宁:
“陕回在西宁者丁壮老弱妇女,统计尚二万有奇…当分为三起,约二万人,派队押赴平凉、秦安、清水等县择地安插。…西宁境内自此无客回羼杂之患。”
在固原境内:
“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固原东西山相继平定,所有各处猖乱之回亦多寄孥其间,以避诛戮。此客回之应迁徙者。”
除陕西回民被迁移外,外来不多的甘肃回民也被觅地安置于安定之刘家沟。
经过这样的安置,原本就已接近百万的陕西回民人口,在陕甘回民起义后,“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
4、对于迁徙回民的安置和防范
左宗棠安插回民,为之建城垣、发牛种,“陇人闻大之譁,至有左阿浑之称。”
但他的工作总体上为他在受抚的西北回民中赢得了良好声誉。回民们习惯使用“左宫保”这样的称呼,“当时左宫保安民,发给回民土地、口粮、农具、牛等物。”
河湟回民长期有谚语曰:“左宫保的章程劈两半”,是说左宗棠办事公正,回民德之。
平心而论,“于九死中得此生路”的乡野回回农民远远只是传统政治统治下的草根臣民,过去与官军、官府的战争和全面对抗并未使他们在宗教意识和政治认同上发生太大转变,他们与清代统治者的关系也远远没有发展到阶级斗争意义上你死我活的地步。
“善后”是将回民从起义状态向臣服于帝国的民众状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达到这一目标,则莫过于注意在官方统治上抛弃成见,重新强调“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的原则,对受抚回汉民众一视同仁。
其时,军力强大,事权专一,左宗棠通过处理一些代表性的案件,向西北各级官员和汉回民众强调了他的原则。
同治十年(1871)三月,灵州发生了“痞棍”(实际是地方汉族恶绅)吕廷桂、苗维新借机讹诈已抚回民,捏造地方绅士公禀,请总统老湘全军道员刘锦棠派兵抄洗的事件。
为此二人沿用故伎,向回民散播谣言:
“谓官军虽暂时安抚,将来仍将尔等杀尽,以致愚回颇怀疑惧。…扬言官爱回民,不爱汉民,种种谬妄,殊堪发指。”
此事上报左宗棠后,左氏震怒,立将吕廷桂就地正法,以昭儆戒,并伤暂统老湘全军提督萧章开,将苗维新解赴营中讯明惩办。
左宗棠积极打击战后的地方汉族主义,力图杜绝由于地方统治原因而再次引发祸端,“间有汉民借词报复者,臣已伤府县随时惩办,断不令仍蹈恶习,致启衅端”。
同治十年五月,在宁夏、宁朔、平罗三县,由于“受害汉民指名控其罪状,”官军按册点验,查获457名曾经起义的回民,“即行正法”。
朝廷在上谕中首先奖励了主其事的金顺等人,同时也注意到其间暗藏的分族报复扩大化的危险,因此上谕特别强调:
“惟附近汉民亦不得有意寻仇,致成衅隙,本日明降谕旨一道,着张曜刊刻謄黄,遍行晓谕,俾汉回永远相安,以副朝廷一视同仁至意。”
“地方官吏遇有汉回事务尤当持平办理,不可稍有偏祖,以昭公允而弭衅端。”
这对于地方统治秩序的恢复,无疑有积极意义。
5、迁来关中的外地汉人
实际上,清军在西北的善后措施不仅施之于回民,一些地区的汉民也同样是迁移安置的对象。
陕西回民被迁移安置后,他们遗留的土地被官方重新进行了分配,而分配的对象则多为汉民。其中既有本地的汉民,也有外地的“客户”。但是,本地汉民分占“叛产”的远远少于外地客户。
原因一在于一般汉民已怕极回民,担心回民会回来重新收地。敢于大量占地的也多是地方豪强。
第二个原因则是由于人口大量减少,许多地方变得人稀地广,关中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大大降低。
外地的客户中大部分都是湖北人,这显然与杨岳斌部下多楚勇,左宗棠、刘松山所率的老湘军、宁夏之战结束后刘锦棠新募楚勇及主陕甘战事者多湖湘人有关。
客户中还有河南人与山东人,则与胜保、多隆阿军中相当一部分士兵都从镇压捻军积累军功并力战陕甘有关。迁来关中的甘肃庆阳人也是客户。
回民西迁之初,湖北及陕西商洛一带的汉民有自发迁至渭城地区垦地的。同治六年(1867)回民军东进,官府被迫试行武装垦殖的办法,把甘肃难民编成队伍,一面种地,一面防守。
在此之先,回民军流动作战于陕甘交界地区,庆阳府各县如宁州、合水、环县都遭受重创。兵乱之后,又值荒年,产生十数万流民。
清军进规甘肃,收抚流民,清洗土匪,陆续将流民集中起来,并在同治七、八年(1868-1869)迁到陕西,安置于回民已迁走的咸阳、泾阳、高陵三县之内。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