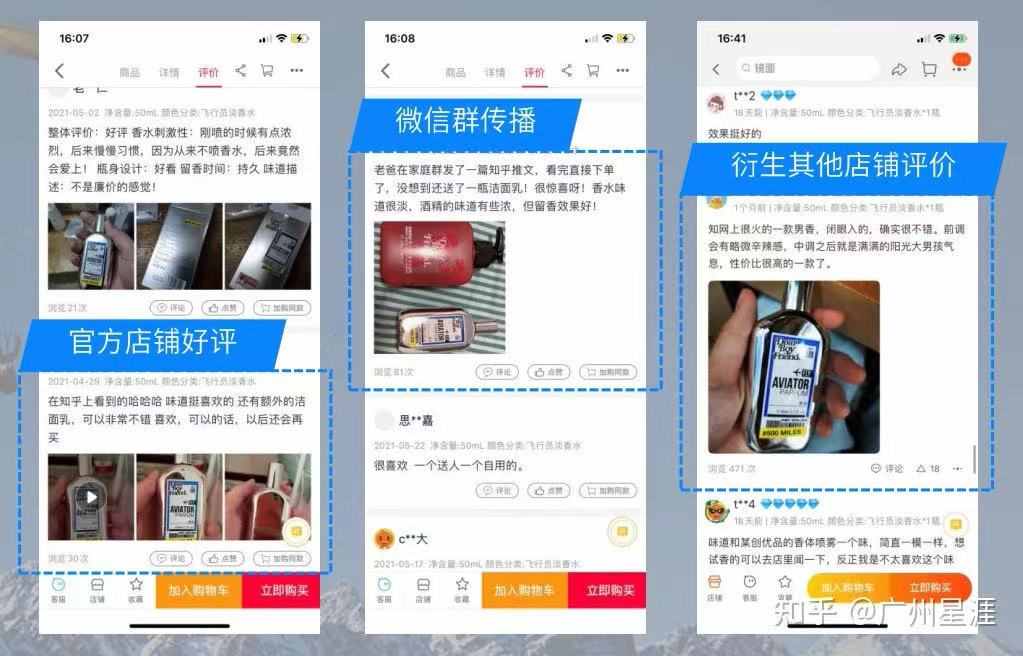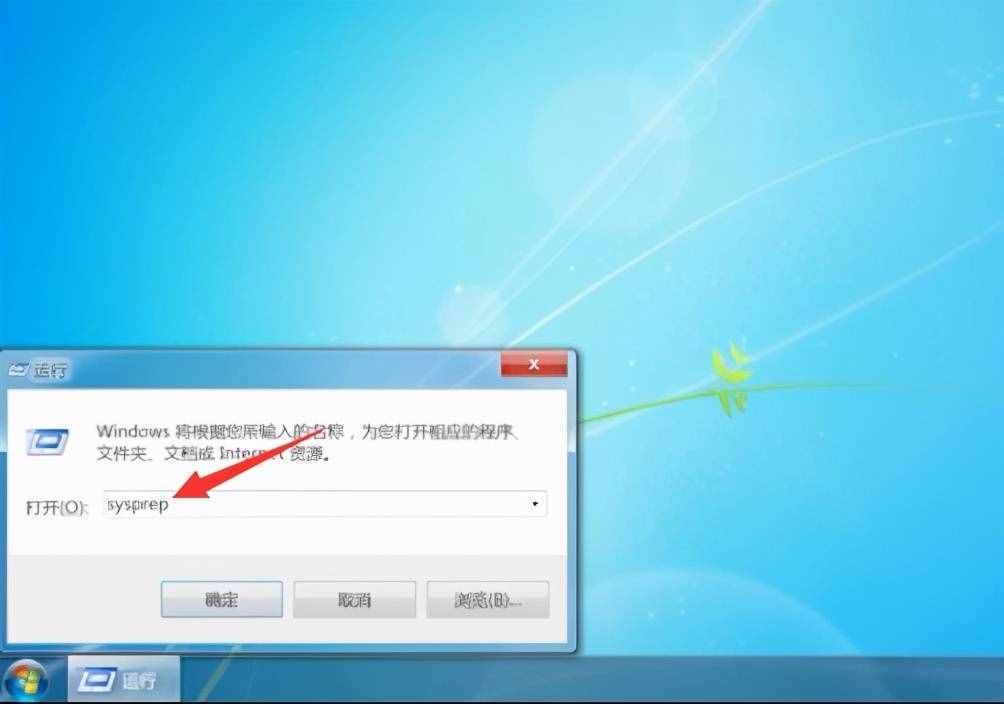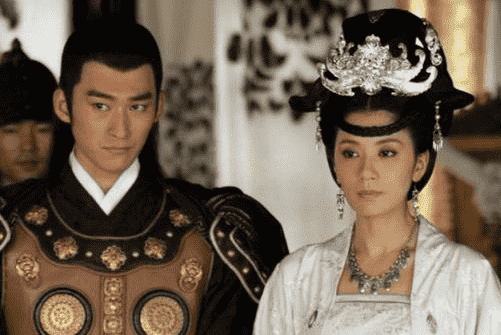“权力”地方文史︱鲁西奇:中国古代乡村的长老及其权力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澎湃新闻的《地方文史︱鲁西奇:中国古代乡村的长老及其权力》,希望大家喜欢。

2022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鲁西奇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上,作了题为“父老:中国古代乡村的长老及其权力”的学术讲座。鲁西奇以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深入讨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实质,进而指出王朝国家统治下乡村社会中的长老权力,其实主要来自王朝国家的授予,所谓的“长老统治”是王朝国家统治体系的一部分。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
“长老统治”与“教化权力”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有三种权力者。第一种是“乡吏里胥”,亦即中国古代乡村的“基层干部”,从汉代的里正长,到清代的保甲长等,他们掌握户籍编排、赋役征纳、治安等基层行政权力。第二种可以称为“强人”,亦即中国乡村中“地方精英”,从秦汉时代的村邑豪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乡望,一直到宋元时清时期的居乡绅衿。他们拥有财富、实力,掌握乡村中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第三种就是“父老”,亦即中国古代乡村中的“长老”。他们掌握乡村的教化权力,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三种人互有重叠,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共同构成了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长老统治”的概念。他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时,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可以区分为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四种。其中,教化权力指在社会继替过程中,“长老”对新成员宣教规范的一种文化性权力。“长老”使用教化权力进行的统治,大致相当于“礼治”。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时,费先生提出了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四种权力划分,认为掌握前三种权力的是统治者,其主要所使用的是横暴权力(“一切决定众人有关事件的权力都集中在统治者手上”);而民权则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应当属于同意权力的性质,但是在中国基层的宗族和地方组织中,同意权力的活动极有限,主要的是教化权力。”
政治结构分析中的民权,主要表现在基层乡土社会中,并通过同意权力与教化权力两种方式发挥作用,而教化权力又是乡土社会最主要的“民权”展现方式。不难看出,在费孝通的系列论述中,立基于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是乡村社会建立并维持稳定秩序的重要基础,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统治方式之一。
鲁西奇指出费先生的分析理路,启发我们可以从权力的主体(权力者)、权力对象(被控制与剥夺者)、权力方式(教化)与权力结果(通过传承社会规范,控制或影响权力作用对象的行为)等方面,考察乡土社会中权力的根源、运用及其意义,分析乡土社会的“自治”机制。
然而费先生并未对“长老统治”作出明晰的界定。因此,如何进一步讨论、运用、发展费先生的研究,如何将社会学方法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如何将“长老统治”“教化权力”等范畴及其分析理路应用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之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
鲁西奇认为必须弄清以下问题:(1)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人是乡村社会的“长老”;(2)“长老”拥有怎样的权力,其权力从哪里来;(3)在不同历史时期,“长老”掌握的教化权力与国家(官府)、士绅等掌握的横暴权力,以及其他民众可以使用的同意权力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或可进一步思考:(1)“长老统治”是否可以看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或统治类型?(2)如果是,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实质若何?(3)“长老统治”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体系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谁是“长老”
“长老”泛指年长而序位在上的人。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每个人既得受长辈老者之教化,同时亦成为长辈而得教化他人。长幼有序,老少传承,社会遂得延续,基本上是文明社会的“自然法则”,在这一意义上并不构成一种统治方式。而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而言,首先,长老要掌握某种权力;其次,长老所使用的权力属于统治权力;再次,其权力的行使有利于统治,属于统治的组成部分。因此,“谁是长老”的问题,就可以进一步明晰为“谁是拥有权力、参与统治的长老”。所以,长老实际是拥有超出家庭之社会权力的“父兄”。各家之父兄代表本户,参与议事决策,形成“父老”阶层;而在“父老”阶层中又有才干出众、品行优秀者,为众人所钦服者,被挑选成为父老阶层的领袖。
秦代的里老、汉代的里父老,均从里中诸父老中选任的,高年、有道德、中赀是选任里父老的三个标准。汉代在里父老之上,乡、县各置有三老,亦由官府主持拣选,以年高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为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均不再设置县、乡三老。文献中所见的父老,多是指乡村中有势力者或富有经验者,非由官府拣选产生,大都是有势力的名门望族,与德行无关。
唐代的乡望由县府负责选拔,标准是耆年宿望、谙识事宜、灼然有景行者,且均由官府确认,另列有名籍,是一种身份。里父老,是得到官府承认的村里长者。
宋代部分州县,仍选拔父老,月给廪俸若干,以示尊崇并备顾问。所拣选的父老多出自富裕之家,较多参与地方事务。元代的“耆老”大抵是由官府拣选、征发的职役。
明代按里设置耆宿或老人,官府的选任标准是年五十以上、品行见识众所敬服的老人。“民间户婚、田地、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然耆宿制实行不久,就出现了“耆宿颇非其人,因而蠹蚀乡里,民反被其害”的情形。
清代彻底废除老人制,兴起并形成了乡约制。乡约更进一步地受到乡村绅衿、地主豪强或宗族势力的控制,越来越背离以年高德劭之父老实行教化权力的宗旨。
总之,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与官府相配合发挥统治作用的“长老”,包括秦汉时期的县乡三老、里父老,唐代的乡耆老、老人、父老,宋代的父老、耆老,明清时期的里耆宿、里老人、乡约等,多由官府选择年高而有道德、且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父老充任。
“长老”的权力及其根源
汉代乡、县三老与里父老的基本职责都是主持礼教,推行教化,其所传布、主持之礼教是王朝国家的礼教,并非民间之教。他们参与调解民间纠纷,协助官府推行某些政策法令,盖由其教化本职扩展而来。同时,还要参与户籍编排、赋役征纳以及道路维修、水利修治等事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父老”作为家族或宗族之长,实际上控制着乡村社会。其权力并非来自官府,而是因为其宗强人众、田广财富,甚或拥有部曲武装。
唐代诸种乡望、耆老、父老等通过各种途径,以不同方式,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情况,传达民意,同时,亦以其道德言行,表率群伦,影响民众。他们还参与祈雨祷晴、庙宇祭祀、建桥立亭、刻碑彰功等公益活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礼义教化的实际作用。父老也参与县乡的定户,以确保评定户等公平。
宋代的父老,参与农田、水利、祈祷雨晴及户籍户等等方面参与乡村事务,并反映民情,评论政策、评议长官,发达上通下达的作用。但其在乡村事务中所发挥作用之大小,取决于官府的需要与具体措施,其对于地方事务的参与,多是其教化职能的具体表现或延展。
元代耆老的地位与作用,似较宋代较高、大。然其权力并非来自官府的授予,而更多地来自其财富、影响。当王朝更替、社会变乱之时,使乡村耆老得以传承其教化之权与功能的,是儒家的传统。
明代按里设置的耆宿与老人,职责的核心是审理民间词讼。老人审理民间词讼的权力,来自王朝国家的委托。老人劝善教化之责,反而由其审理词讼责任延伸而来。乡约制度中,约长(正)亦全部由官府拣选任命,其地位、待遇与职权,亦全部来自官府。
不难看出,历代由官府选任的三老、父老、耆老、老人等,均以教化为其基本职责,受命传布王朝国家的礼教,亦参与调解民间纠纷、编排户口、征发赋役等。
教化权力与乡村权力结构
秦汉时期县、乡、里三个层面的权力格局,大抵皆由官府(县令长、乡啬夫或有秩以及游徼等、里正)、长老(县乡三老、里父老)、富豪以及普通民户等四方构成,分别代表着行政权力、教化权力、经济权力以及(不得不)同意的权力。官府与长老掌握行政权与教化权,居于上位,而官府为主,长老为辅;富豪(富裕阶层)与普通民户都是被管理、教化的对象,居于下位。
魏晋十六国南朝的诸种父老、长老,乃是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者。乡村的权力集中在他们所代表的豪强大族手中,国家与民众力量都较为弱小。
唐代耆老、老人是官府挑选的,故地位与权力就受到官府的很大制约。即便在地方公益事务中,乡老也并不具有主导地位。
宋代乡村的权力格局,相当复杂:州县吏所代表的朝廷,以及奉其戒令的里胥乡老,构成施令的一方;“部民”为接受禁令的一方,包括“豪强之族”和“蠢兹黎庶”,富者和贫者,其中,“乡老”与“胥吏”一起,执行州县官员的命令,发挥“协助”官府进行统治的作用。
元代的耆老更多地介入乡村行政事务,其行政权力有所增大,然其教化职能则渐渐丧失,而且得不到官府的尊崇。因此,在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中,“长老”的教化权力事实上越来越模糊,并逐步衰退。
明代洪武年间颁布的《教民榜文》首先区分了县官与老人、里甲在司法事务上的不同责任,本里老人负责民事纠纷案件审理,重在词讼教化。
老人制与乡约制在演变过程中,逐步融入基层行政系统,失去其自主性。从明中后期到清代,各地乡约组织千差万别。而其演变的总体趋势,则是其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实际上逐步演变为与保甲制合为一体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
概而述之,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主要由乡吏里胥、长老、富豪乡绅等三方构成:乡吏里胥代表官府,行使以户口编排、赋役征发和治安为中心的行政权力;长老受官府委托,掌握教化权力;富豪乡绅占有财富和资源,和官府相配合,行使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
“长老”的权力及其实质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长老”及其权力,有两个源头:一是乡村社会自身,特别是家庭以及“村落共同体”内部,它基于建立、维护与传承其内在秩序的需要,赋予“长老”(父老、父兄)以尊崇的地位,以及规范言行、维护秩序的权力;二是王朝国家,它基于其政权合法性及政治社会秩序的需要,自上而下地,逐层传递对于“长老”的尊崇,并赋予其演示、传承国家礼教的职责以及据此规范社会行为的权力。
因此,实际上中国古代乡村中的“长老”是一种得到官府确认的身份,是经过官府拣选的。普通家庭中自然产生的父兄及其权力是“自然身份”和“自然权力”,其对于家庭成员的掌控权力,既来自家庭共同体本身,也来自王朝国家对于家长制的肯定、鼓励,以及对于家长权力的赋予。长老被赋予并行使的教化权力基本上可以看作为行政权力的辅助性权力,它在本质上也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权力,是统治权力的一种类型,是王朝国家统治权力的组成部分。
教化作为长老的核心权力与职责,其均来自王朝国家的授予或委托;参与词讼审理、赋役征发、地方公益等事务,均由其教化之权延展而来。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长老的教化权力,虽然历有变化,然其总体趋势,是递减的,并逐步向兼理行政事务的职役演化。乡村的教化权力,逐步转移到在乡绅衿手中。
最后,鲁西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考。在一个普通家庭中父兄的权力如何?其主要表现在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权、家庭事务的决定权和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而这些权力有三个来源:一是在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生计或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三是在户籍体系中的户主地位。以上诸方面,都值得深入分析。目前,鲁西奇正在分析不同时期户主(户人、户首、家长)身份的获得,以及制度规定的户主对于户内成员的权力,他认为家长权力的部分根源当来自王朝国家的授权。
(本文已经鲁西奇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