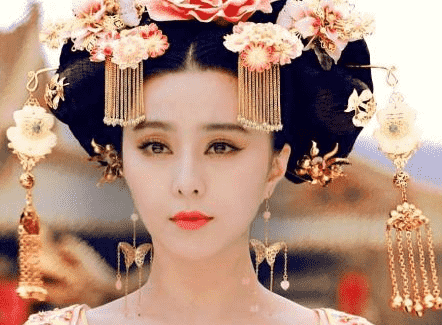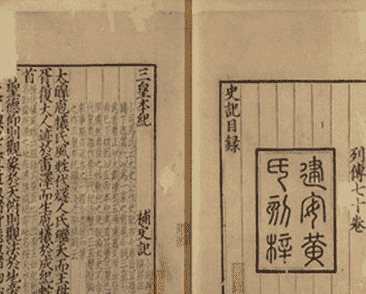“大象”叙诡笔记|晚清最后一只大象的下落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澎湃新闻的《叙诡笔记|晚清最后一只大象的下落》,希望大家喜欢。

在古代笔记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志怪传奇,这里有个一想即明的“潜规律”:越罕见的动物篇目越少,比如麋鹿;越常见的动物篇目在其次,比如猫狗,而篇目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与人不远不近且略带神秘感的,比如狐狸……所以,常人难得一见的大象,极少有志怪的故事,在古代笔记中偶尔一现,往往都是“非虚构”的内容。
《万国来朝图》局部,清代
一、大象当上“安保员”
有关研究证明,汉唐之际,大象在中原地区就已经成了多为官方豢养的稀罕物,比如《新唐书》中记载:“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养大象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或仪仗,更重要的是安保。胡玉远主编的《京都胜迹》上说,相传大象能“鼻验铁器”,所以一旦有刺客携带武器经过它的身边,它都会甩着鼻子嗅之,是故帝王临朝时,相关的管理人员必率大象列队立于朝门左右进行“安检”,“钟鸣鞭响,六象严肃分立两旁,四足不动,若有携带武器者,必被大象鼻摔于地,然后就擒”。百官入内后,它们就以鼻子相交而立,示意朝门封闭。
朝廷豢养大象的地方,名曰象房。笔者所读之笔记,多以为象房在北京之设是在永乐、宣德年间,比如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就说:“当由成祖平安南,以象入贡,始建此。”此记其实不确,因为元人熊梦祥所编《析津志》中就有“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的记载。只不过,象房在明代从金水河北转移到了宣武门西。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象房在宣武门西,城墙北,每岁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洗濯。”此地即今天的北京长椿街一带。笔者幼时,但凡去长椿街,长辈们总说“象来街”,其实就是沿袭了旧称。
《长安客话》
洗象一事,在晚明浸成盛会,刘侗、于奕正所撰之《帝京景物略》记载:“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紏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者两岸各万众,面首如鳞次贝编焉。”这里的“象奴”是指大象的饲养员和训练员,因为大象初运到京,野性未驯,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不可以上朝的。《元史》有载:“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说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有一次打猎回城,乘坐大象拉的车辇,结果有个伶人表演狮子舞来迎驾,把大象给惊了,狂奔乱逃,谁也没办法,多亏有个大臣上前阻拦,后面赶来的人砍断了连接车辇与大象的绳索,才使忽必烈平安无事。《池北偶谈》中的一则笔记更是提及了康熙皇帝目睹的一次“虎象斗”:“康熙中,驾幸南苑,观象与虎斗,虎竟为象所毙”——可见大象发起脾气来,不是闹着玩儿的。
《乾隆洗象图》清代,丁观鹏,纸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日下旧闻考》记载:“盖象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可见其虽称之为“奴”,但因职责重大,级别不低。不仅如此,其实象奴还有“外快”可捞。晚清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就说,有人想进象房看大象的,必须要以钱贿赂之,而象奴教给大象的一些绝技,比如甩鼻子作铜鼓声,那就得另外加钱才能观看,“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必斜睨象奴,钱满数,乃俯首昂鼻,呜呜然作觱栗、铜鼓等声,万众哄笑而散”。
二、一只大象活活饿死
象奴有象奴的收益,亦有象奴的威风,清代学者方朔在《洗象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蛮奴驯象如调马,以钩为勒随上下;蛮奴洗象如浴牛,拳毛湿透归悠游。”象奴对大象的训练,重点当然不可能放在杂耍上,而是要教它养成好的规矩。
据传这些大象会按照训练的水平分成不同的品秩,而根据品秩享受不同的待遇,吃的、用的都不一样,在皇帝上朝时的站位也不一样。如果犯了过失,比如不该叫的时候叫了,不该动的时候动了,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上有提到“有过伤人者,则宣敕杖之”,两只大象会用鼻子缠住受杖大象的腿,将它缠趴在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此外,大象还有一股傲气,如果有一象生病不能在上朝时侍立,那么象奴不能随便拉头大象来顶替,必须牵着生病的大象到象房里,找到可供替补的大象,“面求代行,不然,终不往也”。
《梵天庐丛录》
大象生病,如果病重,耳朵里先会流出油状物来,“名曰山性发”,这个时候象奴知道大象恐怕是不行了,就先以粗大的绳索将它捆绑住了,然后由“管象坊缇帅申报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验,发光禄寺”……这么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半个月,大象早就病死了。巨大的尸体腐烂后,“秽塞通衢,过者避道”,那种景象,不仅惨不忍睹,还臭不可闻。
清中期以后,南方长期战乱,没有大象进贡到京,朝仪就渐渐中断了用象,而由于财政支出的紧张,象奴的收入也日益减少,在驯养大象上更不用心。光绪十年,一只发疯的大象突然冲到西长安街上,伤人又毁了不少东西,据说疯象用鼻子将一个太监卷起来抛到城墙上,此人当即死亡。折腾到很晚,銮仪卫才将这只大象捕回去。这之后,大象们慢慢死去,“象房余一老象,时人有南荒遗老之咏,至己亥,此象亦毙,遂永绝响”……
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耗资两万九千两白银,给慈禧献上一百三十多种动物,其中就有两头大象,还高薪聘请了两名德国人看管。由于粮草不足,其中一头竟被活活饿死了,慈禧对此十分不满,产生了要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养这些动物的想法,恰好有大臣奏报建立万牲园,于是得到了慈禧的批准。1907年农历六月十日,作为农事试验场一个构成部分的万牲园先行开放,售票展览。宣统元年的《农工商部章程》记载,万牲园内“建有兽亭三座,兽舍四十余间,鸟室十间,水禽舍、象房……各一所”,而象房就是为那另外一只活下来的大象“大力”建造的。
而这一只大象的“结局”,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清朝万牲园
三、“大力”死后惨况种种
笔者最近读到一本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过万牲园园长的著名文史作家夏元瑜先生撰写的回忆录,其中一篇谈到了“大力”的下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北平动物园(即万牲园)的一位工友下毒毒死了“大力”。“大力”中毒后,毒性很快发作,时局混乱,也找不到合适的兽医,大家只能看着“大力”一点点咽气,“大力”临死前“还用鼻子揪着前任管理员孙久山的手,相对垂泪,凄然永别”。
按照北平动物园的惯例,死了的动物都要做成标本,当时正值盛夏,又赶上侵略军入城,出入城门很不方便,动物园在西直门外数里之遥,大象又不是小动物,做标本要剥皮,必须翻来翻去,一两个人根本翻不动,怎么办呢?夏元瑜灵机一动,想到卖羊肉的会剥皮,于是约了六七位给动物园常供饲料的牛羊肉老板来帮忙,这时距离“大力”死去已经过了三四天,“死象臭了,肚子鼓得像座小山……以一公里为半径,全在臭气笼罩之内”。夏元瑜和那几位羊肉店的老板,十几名杂工,就在臭气的中心待着,照理说常人早就被熏跑了,但老北京的习俗,既然答应了帮忙,绝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大家用纱布做了厚厚的口罩戴上,口罩中撒了“太伤避瘟散”,才能继续工作。
“红头绿身、闪着金光的大苍蝇,不但成千上万地来观光,而且大量地生孩子,又白又肥的蛆爬满了象身,望过去好像会冒白气一般。”工人们泼了几十桶石炭酸水,扫出了整整四大筐的蛆,然后用极粗的麻绳拴住死象一侧的前后肢,十几个人一起拉,把侧卧的死象拉得肚子向上,然后开始剥皮。“第一切线是从象的鼻端内侧开始,一直到尾巴尖儿为止;第二切线是从左前脚心垂直横过腹面到右前脚心;第三切线是后肢的左右脚,也就是横那条中心线。”员工在象肚子上把该切的线用粉笔画了出来。
开始动刀后,先切开中央线,“腹部的皮比胸部薄,只比皮鞋后跟略厚些,切开处露出下面一层灰绿色的腹膜——内脏腐败则腹膜变绿”。谁知这一下出了大意外,死象的腹中气体膨胀,之所以没有破裂,却因为有层皮包着,这一刀切开,顿时大裂,站在腹面上的一个人一下子陷到腐烂的肚肠里去了,众人赶忙将他捞出来时,此人已经臭昏过去了。
一般来说,一只死去的动物可以做成两件标本,一件是用皮做的外形标本,一件是用全套骨骼做成的骨骼标本,但“大力”被剥皮煮骨之后,因为战乱,皮和骨就那么搁置了很多年,也没做成标本……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经为朝仪用象一事从盛到无而感慨:“区区小点缀,亦有六百年以上之史实,且与吾国声威制度之消长相关,弥为叹息。”却不知山河破碎之时,“区区小点缀”又岂止消长,只怕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