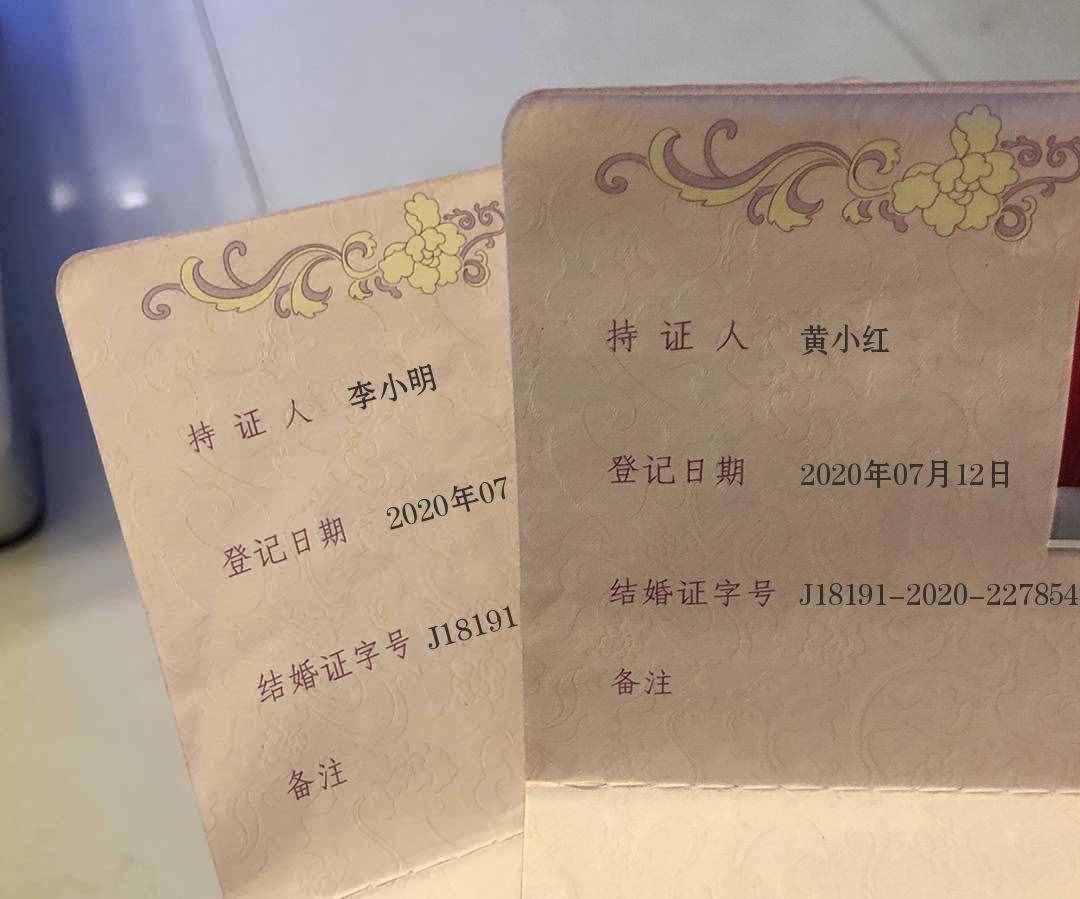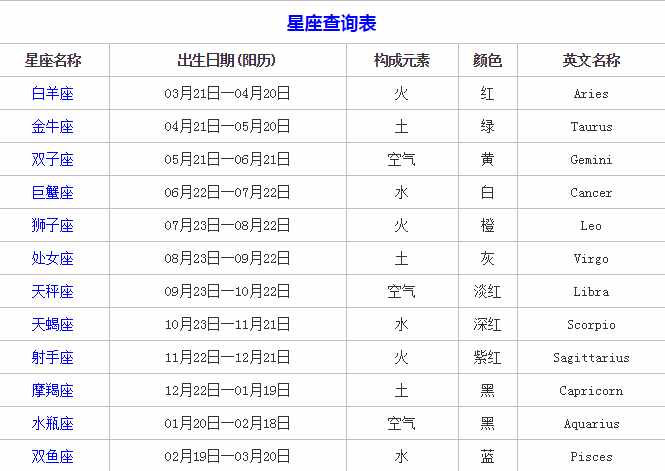“诗史”清初“诗史”为何与文化“救亡”息息相关——是士人的心灵支柱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历史陀螺V的《清初“诗史”为何与文化“救亡”息息相关——是士人的心灵支柱》,希望大家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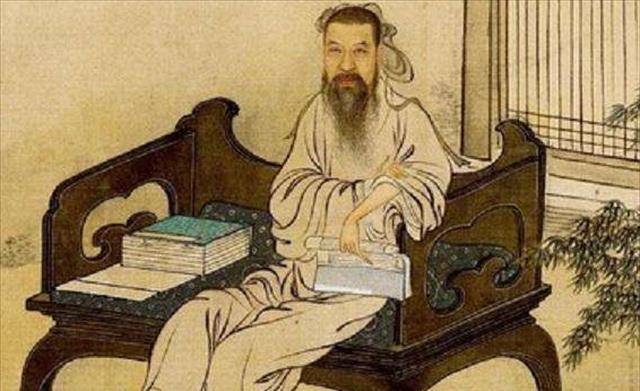
总的来说,清初“诗史”论的主要围绕“诗史”的“纪史”“纪心”功能、“诗旨”表达和“诗体”规范三个方面,“诗史”话语自身的延展只是清初“诗史”观念的突出现象,蕴藏其下的是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民族智慧的生发。
现实层面上来说,清初“诗史”与文化“救亡”息息相关。清初士人乃至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于此次文化“救亡”中。
内容是文化救亡的现实基础、“救”成什么样、如何“救”,“诗史”的众多内涵也在文化救亡中得到全面释放,这也是“诗史”观念流行于清初的根本原因。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的深化
一“诗史”与“诗统”
明末清初的时代变革中,清初士人面对“正统”“道统”“诗统”等各个统绪的破坏,意图重建统绪。“统绪”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着人们当世的思想状态和人力、资源倾向,清初对“诗统”的重建基于其对王朝正统、王道正统和诗文传统的回护与再认识。
1王朝“正统”观的忠义维度
“削发”“嘉定三屠”等事件是清朝统治者为巩固朝纲针对汉族士人所进行的武力镇压,而明末清初上到遗民、下到各地义军都打着恢复王朝“正统”的旗号来捍卫明王朝的合法性。反清复明的力量直至康熙二十二年才宣告结束,其间各个政权为了顺应天命、确立正统,积极转变意识形态以适应汉族士大夫观念。
以天命“正统”为依归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反映着大顺政权、南明政权、大清政权的执政心态,当“正统”观念与“忠义”精神不可分割时,清廷借“救民”“忠义”之名号立国也为“诗史”话语的留存奠定了现实基础。
“天命”是古代“天子”上受命于天、下履职于民的统治思维,面向天要受命于天的规律性、创造性、启示性,面向臣民要践行天道,以履行仁义、治理疆土为主要职责。在大顺进京、南明偏安、满汉“三藩之乱”这样频繁的政权斗争过程中,清廷通过两种方式先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而确立了清朝的统一。
2诗歌选评中认定杜诗典范
诗歌传统的认定是各代诗歌创作时的审美旗帜,诗学视域内对诗史中诗统的理解是清初文人立足诗歌史、阐明自己艺术取向和审美典范的明确标志。
清初诗统重构有着时局变幻下扭转文风的现实特点,即不同于历代诗统的趣味表征,清初诗统的确立更是一种策略性的抉择。杜诗及“诗史”被认定为诗统,有两个主要原因:从儒家传统对忠义价值的肯定来说,“诗史”符合当时遗民情绪的表达。
因其社会历史性成为流行的诗学话语;从诗歌创作风格、诗法修辞等诗学角度来说,清初诗论家也通过对诗歌传统的反思、整合来筛选典范,杜诗则通过了清初文人的修正眼光,在风雅旨趣和诗法诗艺上依然成为当世的审美理想,保持了自宋代以来的宗主地位。与此同时,众多清初文人也把他当作诗统中不可或缺甚至承上启下的代表。
二“诗史”与“诗教”
1.“真性情”的诗学追求
清初历经世变的文人在秉持“诗史”精神记录社会变迁、抒发黎民之悲、慷慨激愤的笔触之下,普遍认为抒发真性情是诗歌的本质,同时,有识之士回归传统诗学观念,从诗歌文体、内容上肯定了“真”“性情”的抒发不仅是诗歌自身功能的发挥,更是易代思潮与人性自然表达之结果。
清初“世变”后遗民“诗变”在诗学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对“真”诗、“性情”诗旨趣的标榜和再认识,体现出史家的现实主义品格。
清初遗民重视“真”诗,对“真”的追求有其现实历史原因。一方面是对晚明拟古因袭之风和徘徊于“格调”的伪情进行扭转。
另一方面为满足社会矛盾冲突中的人抒发强烈情感与真实表现的诉求,其三是借此肃清清初士大夫遗民群体中所存在的“文辞欺人”“文行悖离”的虚伪风气。对于一些以“遗民”自称、不愿投身异朝的志士仁人来说,以“真”作为诗歌追求是对自身文风和人格道义的必然要求。
2“诗可以怨”与“温柔敦厚”
清初遗民倡言世变而诗变,以此肯定诗歌变风、变雅、诗可以怨的合理性。从诗学话语内部来说,清初遗民论“诗变”多借诗学中“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等问题提出创见,当世诗歌也有如申涵光语:“多慷慨不平之音。”
从影响诗歌风貌的外部因素来看,“世变”与“诗变”也即“世运”变则“诗运”变。清初遗民肯定世运与诗运的关系,不仅能够以政治衰亡的时运理解乱世之音“诗可以怨”的创作风貌,还反向发掘出诗歌变风、变雅和“诗可以怨”的存在意义,也即隐藏于诗歌背后的历史表征功能,发挥了清初诗歌、诗论中暗含的“诗史”价值。
同时,遗民将世变后哀怨不平的诗也归入温柔敦厚的范畴,使“温柔敦厚”与“诗可以怨”话语突破了以诗治政的君臣视域,指向救亡天下、实现诗教的使命。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下的创作实践
如果说人文精神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抽象概括,那么“诗史”精神就是对某一时期“诗史”意识指导下的作品的抽象概括,中国学术和文化对于史学素来重视,但从不囿于体制唯独以史书的形式来保存历史文化。
对于并非符合史书体制却具有史料价值的文本有极大的宽容度,从而有“诗史”“野史”甚至是墓志铭、方志、年谱、碑传都可以成为发掘史料的载体,历数各代的文化作品,清代文化事业的繁荣无出其右,清初“诗史”观念深入人心,可以发现史料的载体愈发多样而丰富。
一清初创作风貌
清初士人针对晚明政局的疲弱之态代之以积极的社事活动和对晚明心学弊端的反拨,同时大力倡导恢复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这直接影响了清初创作的精神风貌,当然清初文学创作也有其独特的情感特征,如强烈的使命感、生命的悲怆感等。
1.易代时局与清初文坛新面貌
易代时局给以明遗民最为沉重的打击和与之相应最为深刻的反思。从事实上来看,压死骆驼的从不是一个最后一根稻草但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即使一件小事的发生缘由都很难由条理的逻辑推理、论证出来,何况是历史的剧变。
面对明末“天崩地解”的历史境遇,遗民志士无暇有宿命论似的哀伤,唯尽人事、听天命尔,故此明清士人对明亡原因的追寻不一定是全面的,但是尽其所能为的。
文坛领袖在易代时局之下也担负了引领大批士人抒发精神气节、平衡复国与自适情绪的责任,文学创作的意义在清初尤为复杂。随着崇祯年间遍地而起的农民暴动与满族的日益壮大。
明王朝真正进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危亡局面,复社继东林而起,除了接续东林党人复兴古学、重振气节的东林精神和政治文化活动外,有意识的将全国各地的文社与文人活动组织起来,形成真正独立于南明疲弱政权的组织体系,各地文社互有联系,钱谦益等文坛宗主虽不在复社成员名录中,却是全国士林的精神领袖,为其后全国文人大会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遗民心态下经世致用的创作追求
与晚明陷入自适与与自修独体心性的士人心态不同,东林党和复社等遗民文人标举“经世致用”的责任意识,谋求改变国家、民族、万民的命运,即使复国无望也要为汉民族文化的留存和来日的重建做好精神基础和思想储备。
“经世致用”有这样两个基本要求,其一是入世,也就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下“通经致用”的理想和传统,其二是有目标,即“讲事功”。一体一用,体用兼备。在清初表现为士人有明确的入世倾向、有缔结社约共同进退的结社活动、有武力和文化上积极抗清的目标等,文化重建方面遗民士人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编纂文献的学术经世则基于他们“卫道救时”、积极入世的热情和“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以“梅村体”、《桃花扇》为代表的诗文创作
有鉴于明末复古诗论和标举性灵的时代氛围渐趋脱离现实,吴伟业在“务为有用”的宗旨下记载诗人的事迹,于《抚论集序》《彭燕又偶存草序》《宋直方林屋诗草序》等诗论中强调纪录当世“人”“事”的真实情况,“以诗存史”是他基础的“诗史”论。
在文学实践中,吴伟业是清初直录当时史实、细致描写当世社会风貌和人情冷暖的“诗史”代表,其诗歌也因“心史”的深刻性而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1.“梅村体”的诗歌创作
“梅村体”的诗歌是清初典型且数量巨大的“诗史”创作,主要表现在夹叙夹议的内容、叙事组诗的结构和叙事手法、丰富的用典、与“诗史”精神相呼应的道义情怀以及政治美刺的自觉,这些特征与第一章所述“诗史”之内涵相契合,除此以外还有吴伟业自发的“心史”的实践。
正因吴伟业对“言”与“旨”的不懈追求,立足于诗、曲、词的相通性上,他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了长篇歌行、组诗、近体诗甚至是长篇剧作等多种文本形式,当然,体裁变化背后不变的仍是“诗史”意识和“心史”内涵。
2.《桃花扇》的剧本创作
《桃花扇》是清初士人阶层最直接、最复杂遗民心态的熔炉,孔尚任对其创作的意图和所关注的人物有很清醒的认识,在《本末》篇中说:“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也,灯酒烂,唏嘘而散。”孔尚任多有“负其无聊不得志之士”的亲朋,借个体之间的恩怨离合寄寓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之感是《桃花扇》。
表达遗民心志的书写方式,剧本中既有“亡国”与“亡天下”的悲伤情调,又描写政治、军事斗争,兼述遗民的情感生活和政治立场,在反思与感伤中融合了对奸臣误国的理性思考和对忠、义文化的坚定选择,以历史史实作为创作脚本,刻画具有典型特征的代表人物,充分体现其浓烈的“诗史”意识。
《桃花扇》作文在第二十一出《媚座》中批其出目:“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乱治系焉”,从人物刻画上来说,《桃花扇》中专以山河破碎的历史现实中的代表人物为描写对象,包括忠臣义士、遗民文人、坚贞烈女和害国权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