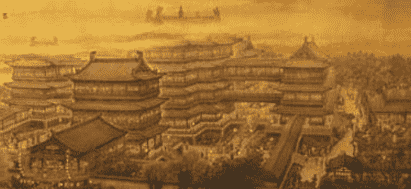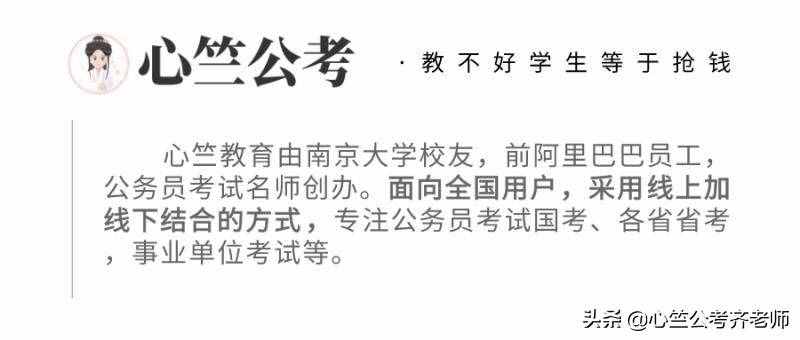一朵白蔷薇(一朵春日白蔷薇的凋零)
一朵白蔷薇(一朵春日白蔷薇的凋零)
我从来没有机会在春天看到红色的枫叶,我一直以为,红枫只能出现在“醉染栖霞山”的梦里。
我也很久没有在早上的七点醒来,走在宁静的远郊柏油路,四下里人烟稀少,可我却没有一丝心慌的触动。
这是我生命中难得的瞬间,好像我很久很久都没能与这种至上的清宁言和,或许有很长一段年岁,我都在和弥沙的心境交锋吧。
红枫很美,可是它的生命又那样坚韧,从不协同于风吻的凋零,也因如此,他少了太多机会,走近哪个善于缅怀之人的笔记本。

世间的人,多是不悲不喜,思索来程与去路的确是繁同累赘的事情。
过去的三个月,我也许用自己真实的意念应了一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我看见窗外的雪梅一步一步濒临枯萎,我看见青坟前的海棠一寸一寸拥获重生。
有一天,我独自走在河滨的老桥,春风同我枯槁的面容打了个照面,我闭上眼,感觉到世界的希望,可惜了,我比谁都知道——人类的悲喜的确难以相通。
在希望中的悲伤,比冬季的最后一抹寒风还要冷峻,如同三把相交的宝剑插在身上,把把开刃。

生命中稀疏平常的事物,在我人生中的前十八年,大致粗糙领略。
没有人在意一朵春日白蔷薇的凋零,就像没有人在意一片夏日红枫的绽放,是同等悲难的事情。
如果它们同样拥有体察人情的机会,那么难过便必不可少。
玄武门外的樱花究竟谢了几遍,清凉山的绣球究竟丰腴了几许,我才不紧不慢,等待在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让命运的舟把我推到现在的未名。而我则忠诚地服从于生活的皇冠,像一个偷穿了金缕玉衣的逃兵。

我是一个相信直觉却也痛恨直觉的人,于是我再一次带着预谋的退却出发了。
夏天就快要来了,一瓶几近过期的“鼠尾草与海盐”,我选择带在身边了,它收藏了一座海滨城市最后的夏期。
如果拥有一次调和人生香氛的机会,会有人选择白蔷薇和红枫叶吗?寥寥无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