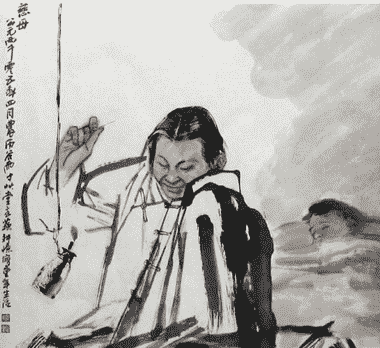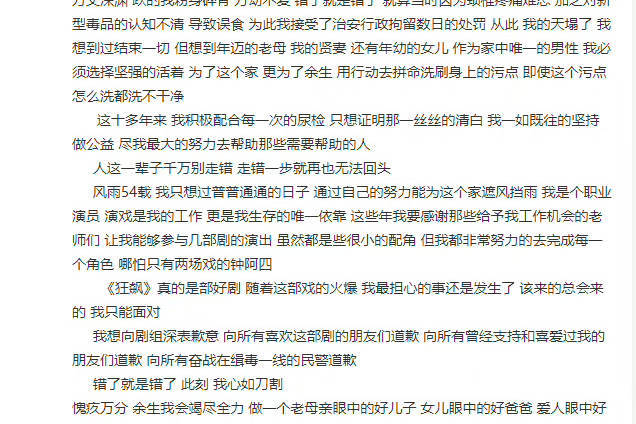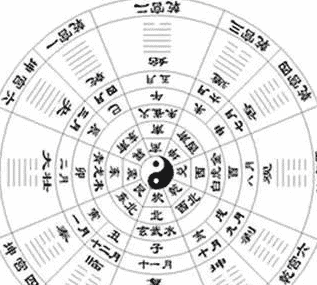“敦煌”用一本大词典全面考证敦煌文献字词再现千年前日常语言及生活面貌|封面专访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封面新闻的《用一本大词典全面考证敦煌文献字词再现千年前日常语言及生活面貌|封面专访》,希望大家喜欢。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汉字汉语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廊里,不断生长、变化、发展,汇聚成现在人们当下使用的“活”的汉语。但也有不少字词,脱离了线性时间之河,像琥珀一样保存在浩瀚古代典籍之中,等待后世去发掘、激活。一本大型字词典正是这样的语言之舟,横渡时间之海,助力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连接。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清末被发现的总数达七万号的敦煌文献,恰好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其体现出来的语言特色,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蕴含着极高的语言文字研究价值。可以说,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古代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俗字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提到敦煌文献,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宗教类内容。但其实敦煌文献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通俗或者世俗类作品,比如变文、曲子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案卷、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它们的作者和传抄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由于这些作品或文书的“民间”或“半民间”性质,从而为通俗字词“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中的语言,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俗字、别字、俗语词之多,保存口语材料之丰富,实为它书所未有。其对于推究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随便打开一个敦煌写卷,往往都可见到若干新鲜的语言成分。在当时底层百姓使用并流通的契约文书中,普通人使用的口语或者世俗用语特别常见。”敦煌学资深研究者张涌泉说。
01
相较于“雅言”
俗字、俗词语等民间口头语词更难懂
传世文献(刻印流传)大抵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有较为浓烈的官方色彩。同时,印刷是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多为四部典籍及与政治、宗教有关的高文大典,很少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敦煌、吐鲁番写本文献大多出自底层的官吏、学郎、经生等凡夫俗子之手,未经后人校刻窜乱,大众化,原生态,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带有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内容无所不包,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普通人日常交流用语及用字的面貌,显得极其罕见而珍贵。
传统训诂学主要是为经学服务的,所重视的是“雅言”,而对跟老百姓相关的民间口头语词,向来不甚重视,所以也很少研究。由于这些口头语词的方俗性质,加上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理解它们的难度往往要比“雅言”大得多。而且,传世文献中的疑难字词,有历代众多的字典辞书可供我们查找检索。而像敦煌、吐鲁番这类新发现的写本文献,遇到特殊词语、疑难俗字、通假字,往往无法在现有的字典辞书中找到答案。
02
几代学人倾注全力
打造敦煌文献语言之舟
敦煌文献被发现后,很多语言文字学家投身其中,致力于释读、破解其中的疑难字词,帮助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的困难。
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原稿正文首页(张涌泉提供)
早在20世纪50年代,敦煌学研究大家蒋礼鸿先生就撰作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变文中一些“不容易知道它的意义”的语词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通释”,为正确校读、理解变文词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蒋礼鸿又带领包括张涌泉在内的几位学生编纂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词的范围略有扩大。在蒋礼鸿的影响下,郭在贻、项楚等一批中年学者及不少年轻学子也陆续加入到敦煌文献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不但范围多所拓展,成果亦颇可观。
20世纪80年代初,张涌泉在蒋礼鸿的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太平广记〉引书考》,就对敦煌文献里的俗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郭在贻的指导下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敦煌变文校读释例》,更是有不少篇幅直接与敦煌文献的口头语词有关。
之后,张涌泉和师弟黄征在郭在贻的带领下,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更是直接和敦煌俗字、俗语词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撰作《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合集》等著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张涌泉跟随项楚研习敦煌语言文学,耳濡目染,对敦煌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及对敦煌文献校理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涌泉也发现,以上所提的学术成果中对敦煌词语中的解释,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民间契约、判词、发愿文、书仪),却基本上不被关注。另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贴近生活、注重实用的通俗辞书,是当时语言面貌的真实记载。这些词语,不仅对了解唐代前后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等大有帮助,而且以俗治俗,对校读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亦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这些辞书也多未受到前辈学者的重视。
由于存在这种种的局限,使得读者对敦煌文献的校读还颇有隔阂,对一些方俗词语的诠释尚多误解。加上已有的敦煌文献词语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不便,因此,张涌泉决定,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词语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词词典。
03
“男女”“微信”等词语在敦煌文献中意义与今日不同
有时确定一个疑难词的意义需请教七八个专家
2000年,张涌泉申报“敦煌文献语言大典”编纂项目,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后二十余年,张涌泉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夜以继日不断努力,在文献的海洋中爬梳考释,最终完成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写任务,并由四川辞书出版社顺利出版。2023年6月15日下午,这部550万字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正式亮相。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一共收词21939条,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前收词最多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收条目仅1526条。《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不光条目总数多,在释义举例时,编者还把敦煌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相比勘,探源溯流,对大量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错误校释,力图勾勒出每一个疑难字词产生、发展、消变的历史脉络。这样一来,既能解决读者阅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特殊词语理解方面和疑难俗字、通假字辨认方面的障碍,并为汉语史、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全面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方面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被学界称为敦煌学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
以例读书是古人治学的一大法宝。在字词的考释中,《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编者注重字词演变规律的探寻,从纵横两方面勾稽其演变的通例。如“般”条指出搬运的“搬”古本作“般”,宋元以后才增旁作“搬”,然唐代以前古书未见(宋以后所刻唐代以前文献偶有“搬”字,应皆出于传刻者增改);“菓”条指出敦煌写本中花果的“果”多加草头作“菓”,而非指称花果的“果”则不加草头,二字分用的意味明显。诸如此类,都是编写者在深入考察写本及刻本文献字词用法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新知新见,有的颠覆了传统的认知,对读者最为有用。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世无传本的“变文”作品。“变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点像连环画的脚本,故事性比较强。张涌泉说,在变文里很多词语,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跟现在的词义差别比较大,很容易理解错。比如说,“男女”这个词在敦煌变文作品里有儿女的意思,与现在人们理解的常义不同;比如“微信”的意思是“微薄的礼物,谦辞”;“重信”是厚礼的意思;“轻信”是指薄礼;“寄信”则指托人捎带礼物。这都与现在的意思差别较大。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这样的词语,这正是张涌泉和他的编写团队重点搜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释“男女”一词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除了举敦煌文献的三个例子,还有按语,指出这个词汉代的宗教典籍中已有用例。这样就把这个词的解释与传世文献(刻本文献)进行互证,互相比勘,勾勒出词语产生、发展、消变的历史脉络。
一般词典在解释一个词语的时候,只须回答“是什么”就行,但作为一部学术型词典,《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不光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让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敦煌文献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内容无所不包,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需要反复斟酌确定。比如词典中收了一条叫“透贝”的词语,为了准确解释它的意思和得名之由,主编先后通过各种方式请教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东华大学等单位的七八个专家,编写团队又反复商讨,最后才修改定稿。可以说每一个词条的背后都凝聚着编写者的汗水和心血。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内页
04
几十人组成的编写团队全情投入
磨了二十多年的剑终于“出鞘”
从2000年谋划编纂,到2022年底付印出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整整耗去张涌泉和他的团队成员23年的心力。张涌泉说,当书付印出版,这把磨了二十多年的剑到了“出鞘”的时刻,他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人曾说,编词典简直不是人干的活。有了这番亲身的经历,张涌泉才体会到这话说得是如此真切,编词典确实是一件“需要毅力、耐力、认真,不怕烦琐而又艰辛的一项劳动”。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新书揭幕现场(2023年6月15日)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主编除了张涌泉之外,另外两位主编张小艳、郜同麟也是敦煌学的专家。张小艳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她的硕士导师王锳先生很早就关注敦煌变文词语的考释研究。2001年秋,她考到浙江大学随张涌泉老师读博士。当时,张涌泉老师正好申报了这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敦煌文献语言大典”,作为学生的张小艳参与其事,负责搜集撰写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词条。后来,她回贵州拜望王锳先生,说起正在张老师指导下编写《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王先生便将他多年前编就的《敦煌变文语辞集释》赠与她参考。撰写变文词条时,《集释》中汇辑的释义对她帮助启发尤多。
从2001年跟随张涌泉老师读博,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张小艳感慨,“头上的青丝也熬出了华发,但阅读写卷、摘录词条、撰写《大词典》条目的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令人欣喜的是:这件联结着硕士导师、博士导师和我这三代学人的大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看着摆在眼前的这两本沉甸甸的书,我心中默默地说:‘王老师,我们编写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出版了,现奉献与您,请您指教!’”
该词典第三主编郜同麟,如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是一位85后,收到正式出版的书以后,很感慨,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这本词典从启动到出版用了23年,他本人从读博士参与进来也有15年之久,“15年中,至少有三个年头的大年夜张老师都在跟我讨论词条撰写;15年中,为了确定词义不知和老师、师姐抬了多少杠”。
05
专访《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第一主编张涌泉:
“特别感谢四川辞书出版社二十余年的耐心等待”
张涌泉教授在《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新书发布现场(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023年6月15日)
(张涌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整理、近代汉语、写本文献学研究。代表作有《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汉语俗字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学》等)
封面新闻:早在2000年,您便和四川辞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约定2004年交稿付排。但原定交稿的时间一再推延。为什么实际会跟预估差别这么大?
张涌泉:确实是我们一开始严重低估了这项工作量之大、之难。首先,敦煌文献里收录的很多词,跟传世文献中的词意义不一样。在搜集材料阶段,会使用前人做好的整理本,但发现问题很多,需要去查原文核对。其次,已有的敦煌词典收词才一千多条,我们预估自己的这个版本,6千条左右差不多了。结果把整个敦煌文献整理下来竟然有2万条。还有一个原因是,敦煌文献有些公布得比较晚,而且高清晰版本的敦煌文献从2005年开始出,2013年才出齐。种种情况导致完成时间被大大延后。
封面新闻:这本大词典出来以后,有没有特别要感谢的人?
张涌泉:除了感谢我的团队外,还要特别感谢四川辞书出版社的理解支持、审读专家的严谨细致以及编辑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出版社为这部稿子等了二十多年,在交稿后,出版社在杨斌社长支持下组建了高水平的编辑团队,王祝英总编带领冯英梅、杨丽等编辑一起,兢兢业业,精心打磨书稿,并约请了资深出版专家复终审把关,他们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和建议,使词典在内容的可靠性、体例的规范性和文字的准确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周末、假期他们都放弃了,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这部词典早日出版,让我非常感动。感谢他们的专业和敬业。这部书排版难度很大,很多时候他们要守着照排公司调整,真的非常不容易。在设计、印制上,出版社也是费了大心思的,封面调整多次,精益求精。
封面新闻:如果有的人问,像敦煌文献里的有的词不再使用,或者一个词的义项已经消失。我们今天研究它,意义在于哪些方面?
张涌泉:有的词我们现在的确不用了。但如果读古书、整理古书,了解历史和传统,你需要懂它的意思。而且,还可以对我们的语言流变过程多一些了解。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封面新闻:您在浙江大学工作,当时是怎么跟四川辞书出版社搭上线来出版这部词典的?
张涌泉:2000年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可以申请。像大词典这种内容,当时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但时任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社长的冷玉龙,跟我认识,他觉得这是个好选题,值得做。而且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大字典》等好书,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出版社,所以我们就签协议达成合作。冷社长2014年退休后,这个项目出版社方面的负责人调整为现任总编辑王祝英,她对这个项目也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书能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四川辞书出版社二十余年的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