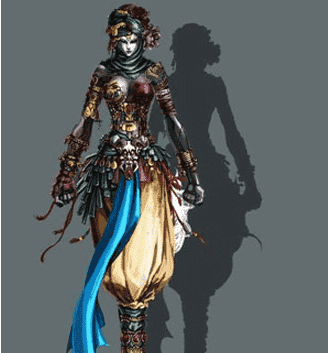“地方”地方文史︱包伟民:地方史研究的四个问题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澎湃新闻的《地方文史︱包伟民:地方史研究的四个问题》,希望大家喜欢。

2022年12月11日,浙大城市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包伟民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上,作了题为“略谈地方史的意义”的学术讲座。他指出,研究“地方”,在史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常识;但在实际研究中“地方”却又常常被忽视,甚至轻视。因此,包伟民从理论出发,并结合具体实际案例,围绕四个问题展开论述:什么是“地方”与“地方史”、全局视野下“区域史”、如何观察的“地方文化”、关于地方史志的几点建议。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彦文教授主持。
什么是“地方”与“地方史”?
包伟民首先对“地方”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一般而言,“地方”(Local)是一个与“国家”“中央”对应的、涵盖了省市县乡村(或市、区、街道、社区)的行政区划概念,这意味着地方史的书写往往与行政层级相一致。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地方”这个概念是在与“国家”“中央”对应之下存在的。如宋人吕陶称“夫人与其子官于地方,凡二十年无恙,一旦归而卒于女之家”(吕陶:《净德集》)。这里“地方”的对应词是“朝廷”,即中央,因此具有明显的行政层级意味。
但是撇开行政区划与行政层级,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地方”还可以有第二层含义,即指地理(自然、经济或者文化等等)意义上的某一地点或一个区块:宋代曾巩在《元丰类稿》中就称“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曾巩:《元丰类稿》卷三〇)。大体讲,这一层“地方”之意,是相对于全局而存在的。
而“地方史”既指某一“地方”的历史存在本身,也可以指那些研究地方历史的工作。包伟民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地方史”,主要指如何展开关于地方历史的研究工作。从上面两个不同角度的“地方”含义出发,可以推知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地方史”的研究有两个的视角。其一,是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基于行政区划展开的关于本地区历史的编纂工作。例如,近年来各地编纂出版的大量某省、某市乃至某县通史等等,各地的新编地方志大致也可以归入此类。传统志书具有保存乡邦资料的作用,现在由于其他信息渠道的存在(例如年鉴以及大量地方数据库),在当今社会大大弱化,因此存在着明显史书化的现象,即志书与史书存在着明显的趋同,故统称为“史志”是合适的。这些基于行政区划编纂的地方史志的主要特点,是其书写的基本路径,一般按全国通史为框架来展开,在大通史的框架里填进地方性资料,使之成了通史的地方版本。有学者批评这些史志为“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或者“国家背景下的地方事件”。
其二,从“地方”的第二层含义出发来做研究,例如江南研究等。现在学界往往习惯于将其称为区域史,意指立足于作为区块的地方所展开的历史研究。其实,所谓“区域史”本来就是地方史,学者们特意称之为区域史,无非是试图与立足于行政区划编纂的地方史志有所区分而已。
最后,包伟民总结,上述区分主要是从其相异之处而言,研究的实际展开中两者又必然具有很多共性。
全局视野下“区域史”
关于地方史研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包伟民强调因为第一种视角,即基于行政区划展开的、关于本地区历史的编纂工作常常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习惯于将地方史视为大通史的地方版,因而不利于深入观察地方历史的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在我国经过长期演变的地方政区中,有些并非按“山川形便”——即按地理区域的自然分界来设置的,而是形成的“犬牙交错”之状——即打破了地理区域的自然分界(周振鹤语),因而割裂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脉络。
区域史的展开需要对研究对象即“区域”有基本的界定,包伟民在此对如何界定“区域”做了详细的说明。首先,“区域”是同质的,区域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它应该是完整的地理单元。除此之外,“区域”还是历史的。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速度与节奏的加快,历史上形成的某一类型的区域会逐步消失,处于该区域中的某些地区也可能会成为其他类型区域的组成部分,或形成新的区域单位。因此,在某一历史时期可以成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在另一历史时期可能就不再是区域史的研究对象了。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是动态的,而不是像自然区域那样相对静止的。
包伟民强调,“区域”常常有别于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尽管某一些“地方”或许恰好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位,例如福建、云贵等地区的一些政区,但多数情况下,政区与地理单位之间的关系仍需小心分辨。只有对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同质的“地方”做研究,归纳它们的文化特征,所谓“地方文化”才有可能成立。所以,区域史是讨论地方文化的基石。
接下来,包伟民以徽州、江南、浙江历史地理区域的变迁为例,说明了在做“地方史”研究时,不要被政区设置所遮蔽,因此忽视更为深刻的地方(区域)特征。我们在讨论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时,应该尽可能按照“地理上的完整性”以及“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这样的标准,从全局视野出发来做观察,才可能触及地方历史的真相。
如何观察“地方文化”?
包伟民在对如今地方文化的研究进行观察与分析后,他发现,一方面,目前实际操作中的所谓“地方文化”,基本上就相当于对某个地方的所有内容的研究,即相当于地方史,其中又常常突出当地的著名人物与景点。另一方面,从各地实践可知,从浙江精神到江苏精神、湖南精神,实际上大体雷同,难以明确区分各自的“地方特色”。这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事实上,传统时期人们在“地方文化”的归纳也有类似情形发生。传统地方志的《风俗》目中,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强调“务本”与“崇文”的传统,齐鲁文化、东南邹鲁都一样。
《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英风澡俗,令德在民”,殷仲堪《季子庙记》之所称也。“风俗泰伯余,衣冠永嘉后”,刘梦得《北固山诗》之所美也。乡党人士平居,习闻先生长者之言,崇道义,尚廉耻,故其立朝致匪躬之节,居闲乐嘉遯之贞,闾阎下庸,亦能以孝行节概自见,详于传志,信难诬也。封内固无千金之家,然服勤务本,閶閶自足,在官者亦喜其庭讼简尠,而无珥笔之讥,四方游宦多寓于此,谓非风俗淳美可乎?或以京口在昔用武之地,而称斗力为所长者,亦浅浅哉。
包伟民认为这些“传统”虽然不一定全为事实,却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卖自夸,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为什么极为相似?是因为“地方文化”的背后,常常蕴藏着大一统的文化理念。
包伟民引用陈支平教授相关研究加以说明,陈支平认为:“大家为了显示某一地区区域文化的历史悠久和优良传统,不知不觉地趋向于中国政治与道德的传统核心,这也是近年大家所说的向心于‘文化大传统’。而正是这一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于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
但在另一极,同时还存在胸无全局的“地方沙文主义”现象,包伟民引用了梁洪生教授的研究对此种现象进行说明。梁洪生认为:“当前做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存在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从区域上先划出一个地方来,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就可以放在视野之外,即所谓‘画地为牢’。其次,按照中国通史的传统模式,再搞出一个省际范围的东西,这就是地方史。现在看来,这种地方史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就地方来谈地方。而且,认为地方史的功绩就在于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研究那些地方独有而‘别无分号’的特色。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此即所谓“地方沙文主义”。
包伟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无法回答“中国”在哪里的问题。第一种远离现实历史生活,第二种零碎化,见不到全局。因此,也就无法从“地方”归纳出“中国”的普遍性。所以,“中国”在哪里与“地方”在哪里,实际上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同时存在。讨论地方文化,毋宁说是要探究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具有某些文化共性,不如说是应该去发现本地区的特性,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求异而非求同。
但包伟民同时强调,深入解剖某一经济、文化“同质”区域,求异——即分析归纳其独具的特征,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究这一个局部,恰恰是为了通过局部来深入了解全局。因为,全局性的特征不可能在悬空存在,只能从“地方”的具体历史文化现象中去发现。也就是,我们必须从相异性中去分析归纳普遍性。他列举了宗族、崇文等现象,这些现象几乎各地都存在,但具体表现又都各有特点。各地在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特点就更明显了。这些特点都有它们的原因,分析其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就是区域史、或者说学术意义上向的地方史研究的任务。
随后,包伟民对区域史、或者说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做了形象生动的比喻——解剖一个麻雀从而了解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仍然是通史框架之下的“地方史”。事实上,每一只麻雀都是独特的个体,它们的生理结构虽然具有共性,但每一个体又都是独特的,不可能存在两只完全相同的麻雀。从各个体的生理结构中归纳它们的共性,说明“麻雀”是什么,才是解剖麻雀应该最终完成的任务。区域史的工作也一样,它是从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之中来抽象归纳整体的“中国”。这个“中国”,放在哪儿都不全是严丝合缝的,但又在基本精神上相契合。同时,所谓“地方”则是从各个不同侧面、各自的特征中反映着“中国”的普遍性。“中国”就在这里,“地方”也在这里,地方史的意义正在于此。
关于地方史志工作的几点建议
最后,包伟民以浙江为例,提出关于地方史志工作的几点建议。
首先,应对本政区不同区块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某种程度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概念化的通史框架,深入地分析讨论某一地区富有地域特点的历史文化现象,并将它们前后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从中归纳发现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编纂出贴近地方、符合实际的地方史。
其次,对本地区与相邻地区关系有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说浙北和苏南之间的关系。以湖州为例,尽管湖州大体上属于太湖流域,但是其西部也有丘陵,那些丘陵地区可能更靠近皖南山区。我们要去探寻这种区域关系,换句话说,力求从本地区的文化特性中间发掘更多能够体现中华文化共性的内容。
最后,在技术层面上而言,如果研究湖州、嘉兴等地区时资料不够,那么可以用苏州的某些材料来做论证吗?对于这个问题,包伟民认为在学理上是可以的,因为苏州跟湖州、嘉兴在文化、经济上具有共性,尽管它们不是属于同一个政区。但是当我们在研究经济文化的时候,用具有相同质的区域资料来佐证本地区的某些现象,学理上是可行的。
在整场讲座走向尾声之际,包伟民总结道,在行政因素干扰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力求以一个全局的眼光来讨论地方史,从各地的相异性中去分析归纳中国的普遍性,从宏大叙事走向具体,走向深入,跳出概念化的中国,深入到各个不同地域。从一般的概念走向历史实际、走向细化、走向具体、走向深入、走向细致。最后才能够深化认知中国这个研究对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史之意义。
(本文已经包伟民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