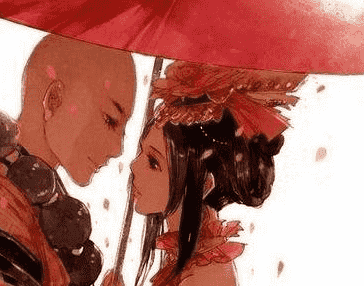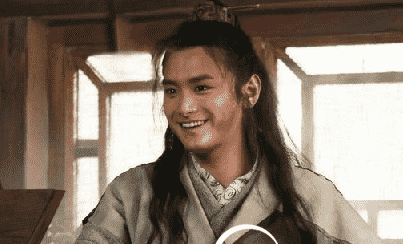“巴金”103岁杨苡:是先生,也依然是小女生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红星新闻的《103岁杨苡:是先生,也依然是小女生》,希望大家喜欢。

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
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因为长寿,杨苡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
杨苡/图据译林出版社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铁凝语)。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也仍然是这本名作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除此之外,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姐夫罗沛霖是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丈夫赵瑞蕻是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
今年,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这也是103岁的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也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图据译林出版社
20年,一场抵抗遗忘的对话
南京大学家属区的小院落里,长着枝繁叶茂的石榴树与腊梅树,白色的小铁门旁,蓝色风铃伴随着微风发出阵阵清脆的声音。屋内,木桌子上铺着白底花纹桌布,柜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猫头鹰玩偶,小收音机里正放着节奏舒缓的《You are my sunshine》。杨苡靠在椅子上,与来人分享她喜爱的歌曲,“我晚上也是11点多睡,听着老歌,我喜欢的老歌,都是那个时候,托塞利的小夜曲呀,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唱的)。”
自1996年起,就在这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她与余斌完成了这场长达20余年之久的谈话,以倾听与记录的方式抵抗遗忘。
据余斌回忆,那一年,杨苡先生知道他写了一本《张爱玲传》,托人告诉他想借一本来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但让余斌没想到的是,平日里话不多的杨先生,私下里却很是健谈,与余斌谈起许多旧人旧事。那些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在杨先生这里,却是在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
第一次登门,余斌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聊了大概两个钟头。
从这以后,余斌变成了杨先生家中常客,听杨先生讲述那些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她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传。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杨苡与余斌合照/图据译林出版社
在杨先生的回忆里,那些在历史浪潮中留下足迹的有名人物,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在杨先生讲述里,却是在她玩捉迷藏时帮她出谋划策,暗暗做手势让自己藏到写字台下的“颜伯父”;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她感念的恩师,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从破棉袄里掉出棉絮的画面……
杨先生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说到翻译《呼啸山庄》也是“好玩”。“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少年杨苡/图据译林出版社
如今,“好玩”也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反正不是为了出版,就是一种玩法。”
但是,谈笑归谈笑,等到了创作的时候,杨先生却是十分严谨的。余斌写成的稿子,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从部分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杨苡都会细细批注。但随后又会给余斌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这让余斌更加感到惶恐:“(杨先生)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巴金与“大李先生”
对于杨苡而言,巴金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
17岁那年,正逢“一二·九”运动爆发,在一团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
让杨苡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她便收到了巴金的回信。“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
17岁的杨苡/图据译林出版社
一开始,杨苡还想要瞒着母亲,到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女儿被一位文学家回信,母亲虽没说什么,但也替她高兴。一直到晚年,母亲还说到了这事,说杨先生就知道玩儿:咱们家那么多故事,你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
也正是巴金的介绍,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便是这本口述自传里反复出现的“大李先生”。
大李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半年时间里,杨苡收到了来自大李先生的四十多封信。她给巴金写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更多是一些小女生的日常流水账:吃了什么,到哪里玩,要看什么电影,遇到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与大李先生的通信,成为杨苡少女时代的小秘密,不仅对母亲,就连好朋友她也没有分享过。她把这些信件都编上号,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
少女时期的杨苡/图据译林出版社
大李先生喜欢音乐。有一段日子,每到下午一定时间,杨苡就会把房间里对街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大声放唱片。母亲对此不解,但无论在房间还是街上都发现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小女生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大李先生每天都会经过这里,那音乐就是放给他听的。
这一段暧昧关系,到底是不是“恋爱”?直到现在,杨先生自己也说不清,这或许成为了她的一个心结。她有时候会说,“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不过这个年龄差在现在也不稀奇。”但有时候又会说,“我们碰都没碰过,外面说我们在谈恋爱,多恶心啊。”
1937年,杨苡毕业照/图据译林出版社
自杨苡去昆明读书后,她与大李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杨先生说,他们曾一起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她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938年7月7日,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在前往上海的船上,同行的师生们一起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一首接一首,一路都在唱。杨苡感到十分兴奋——在敌占区的时候,哪能放开嗓子唱抗日歌曲?等到了云南开远,从窗洞里一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大家便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就成了透明的门帘。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在一片雨声当中,她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唱:“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
西南联大时期的杨苡/图据译林出版社
在杨苡的记忆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就像余斌所言,杨苡似乎一直有一种女生的状态,“如果她的同龄姐妹们还在,她能马上回到学生时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的话题就是当年谁喜欢谁,哪个女孩最好看,哪个男孩最有才华。”
比如联大课堂,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但杨苡却说,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朱自清/图据译林出版社
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给大家上“欧洲文学史”,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大家笑了又笑。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
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她记得的是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具体说了些什么,杨苡早已忘记了,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沈从文/图据译林出版社
杨苡同宿舍有个女孩叫陈蕴珍,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也给巴金写过信。命运很有趣,这个女孩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萧珊,成了巴金的妻子。她们还有一位室友,叫王树藏,是萧乾当时的女友。三个女孩成了极好的朋友,经常“三人行”。有一次去沈从文和张兆和那里,结果把林徽因带来的大肉包子“一个又一个”地吃了。沈从文告诉她们,要读“生活”这本大书,让她们想家了就到这儿来。
杨苡的挚友萧珊/图据译林出版社
和天津相比,虽然当时昆明的房子和街道都很老旧,但对于杨苡来说,记忆里的云、树、山、水,还有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都让当时的她感到新奇又快乐。她说,当时在云南看到的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她还会梦见。
“簪缨之家”的故事
近年来,不少有媒体记者前去拜访杨苡先生,但让她颇感苦恼的是,写到她的稿件总是“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她希望别人眼中的她,是“不高不低”的普通人的模样。
但也怨不得后辈们对杨先生格外尊敬。正如《读库》主编张立宪所说,杨苡的家庭是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杨苡的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中国银行行长。
杨家是大家族,杨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她的家庭和巴金的《家》非常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家里也不是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但是他们家有鸣凤,我们家有来凤。他们家有老爷太太,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
杨宪益、杨敏如、杨苡与母亲徐燕若/图据译林出版社
“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据说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五岁时,男孩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写了一本英文名自传,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
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杨苡的母亲殉节。母亲回答:“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后来,她的孩子们果然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
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
1999年,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2009年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为了“可感,可念”的回忆。
好在,在杨苡的身边,有余斌这样肯反复听她一遍遍念叨琐事的人出现了。
她将余斌称作“小友”,遇到余斌不来的时候,还忍不住挂念几句,或者专门打电话,就为了告诉他今晚第几频道有个什么节目。杨苡说,她和余斌的合作,就是自己不停地说,然后余斌把它们记录下来,“校歌里有一句话,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做到最好。”她估算着作品的完成时间,“等到把这个弄完,我就104岁了。”
所以,当余斌将《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的样书送到杨苡面前时,杨苡忙戴起眼镜高兴地翻看,翻到其中的照片,又忍不住与余斌再一次谈起它们背后的故事。
杨苡说,母亲以前说,要出书就要出巴金那样的,但这一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我母亲应该会对这本书满意。”高兴之余,杨先生眼含热泪,无不遗憾地叹息,“可惜母亲看不到……”
延伸阅读——
也是在今年,杨苡的女儿赵蘅也出版了新书《我的舅舅杨宪益》。在这本书里,赵蘅以日记的形式,通过画家特具的眼睛呈现了舅舅最后十年众多光影流动的生活场景,包括与夫人戴乃迭的相濡以沫、与子女的沟通相处、读书写作、会友人、抗癌治疗以及直面死亡等等。
《兄妹译诗》也由中译出版社于今年6月再版,是两位翻译大家所译英文诗歌的合集,每首诗都是两位先生各自挑选的自己所喜爱的小诗,其中包括了旧版未收录,但杨苡很重视的长诗——拜伦的《西朗的囚徒》。
晚年的赵瑞蕻用深情的笔追忆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刻骨铭心的求学经历:繁忙的梅贻琦“穿着深灰色长袍走来走去”,闻一多的“炯炯目光”,沈从文的“和蔼笑容”,燕卜荪“红通通的鼻子”,吴宓“走路直挺挺的”,钱锺书“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位位大师的身影跃然纸上……
红星新闻记者 段雪莹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