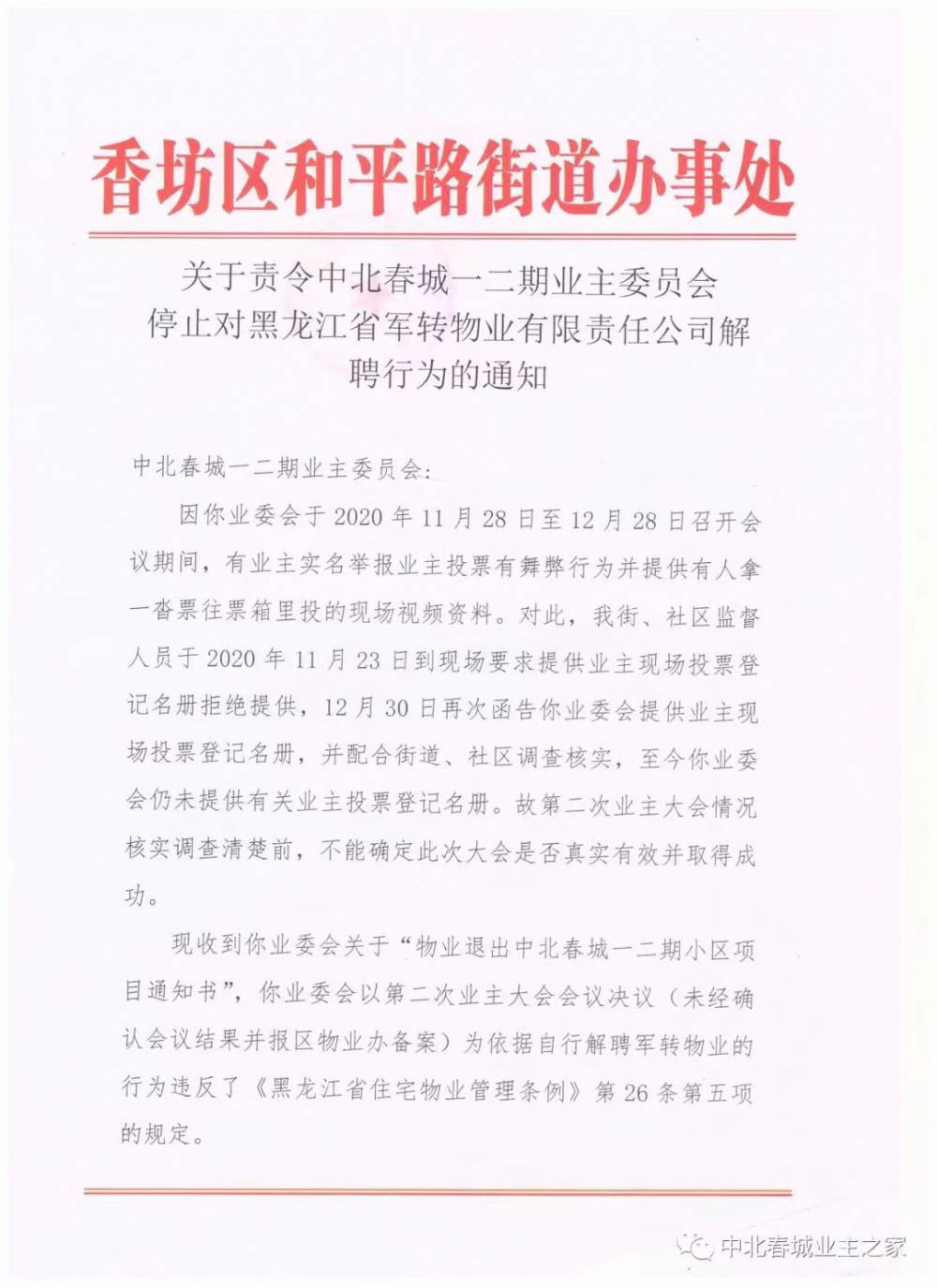“商人”晋商和徽商:一部光荣史,一部血泪史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历史百家汇的《晋商和徽商:一部光荣史,一部血泪史》,希望大家喜欢。

千百年历史里的商人,在生存斗争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
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北山西,南皖南”,最是值得一看的。
安徽黄山脚下,白墙灰瓦的古建筑群,如桃花源般静谧安详。山西民居,因各个大院而名声在外,诸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一南,一北,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而在这些建筑背后,却是明清时期同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
“万里旗亭客,归作田舍翁。”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奔波于万里旗亭之下,有些积蓄之后,多归乡置田建房。山西与安徽,留存下如此多的民居建筑,全赖大名鼎鼎的晋商与徽商。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是徽州,山右是山西。徽商与晋商,历代相承,因乡土僻狭而出走经商,因控制盐业而兴旺发达,并发展为明清时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个商帮。
今天,山西的高宅深院、安徽的水村小巷,都已是人头攒动的旅游景点,配合着人们对富贵人家的想象。或许,只有在难得寂静下来的时候,它们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遗迹,带我们聆听它们低低的沉吟,追忆着那些逝去的故事,深思着一代一代商人的追求与理想。
90年前,中原土地上,一片狼籍。
“中原大战”,号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从1930年的春天一直打到了秋天。晋系军阀阎锡山大败。他在山西发行的晋钞严重贬值,几乎沦为废纸。
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山西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决定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冒着倒闭的危险,把积蓄投入“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
在浩荡的历史潮流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那个由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的特定时代,注定一去不复返。而在大厦将倾之际,“大德通”选择了坚守信义。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士贱商,对商人的偏见,一以贯之。但是,商人有自己的坚持。
乔家开设票号,始于第四代当家人乔致庸。乔致庸时称“亮财主”,带领乔家事业步入中兴,也成为当时晋商的代表人物。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尚义,三才是取利。
乔致庸生于嘉庆年间,死于光绪年间,活了九十岁。国家的兴衰荣辱都看在眼里,乔致庸自然明白,再大的生意,都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
乔致庸一生颇有善行义举,为民开仓放粮,为国筹措军饷。一介商贾,未取文武功业,却也可谓“为国为民”。乔家的理念世代相承,因而当钱财消散的时候,仍有道义深入人心。
与乔致庸差不多同时期,在中国南方,还有一位商人,在商海中度过了漫长的人生,他叫汪定贵。
汪定贵也很长寿,甚至比乔致庸活得还长。与乔致庸继承祖业不同的是,汪定贵是白手起家。他出生在徽州黟县,跟做剪刀出名的张小泉是老乡,也和世世代代的徽商一样,十几岁就出门闯荡。
对于从徽州出走的芸芸商人,历史来不及一一记述。留给汪定贵的笔墨同样不多,但是汪定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在黟县居住的“承志堂”,如今是安徽宏村百余座古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被称为“民间故宫”。
我不禁好奇:一个商人,命名自己的宅邸为“承志”——它要承的,是什么志?
是标榜自己继承先人之志?还是勉励后人继承自己的志向?站在历史的角度,回看往事,是不是更像是代表着全体商人,向世人的明志?
无论徽商,还是晋商,经商或出于生活所迫,或出于传统使然。乔致庸和汪定贵,原本都是把“仕”作为理想的人,然而命运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商”。纵然为商,也要有自己的脊梁。
若不为商,哪有这般丰富多彩、雄奇悲壮的人生?若不为商,怎能体谅世上的百态、民间的疾苦?若不为商,如何把握诡谲的时局、时代的潮流?
在承志堂的前厅,有象征官家威严的中门,在两边的侧门又雕了“商”字图案。这是多么奇特而难解的结合!商人在自己的命运里反复求索,并用自己的方式,一边与俗世和偏见抗争,一边向先人和理想致敬。
历史上,晋商与徽商交集有限,却留下了异曲同工的故事。
山西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山西地狭人稠,徽州山田贫瘠,难以靠自然经济养活自己,于是两地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出经商。
到明代时,他们遇到了同一个发达的契机:盐。明朝为了养兵,先后实行“开中制”和“折色制”,商人可以通过输送军饷,换取“盐引”,获得贩盐的权利。山西人和徽州人,借此成为势力庞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形成商帮,是为晋商和徽商。
晋商不辞辛苦,从江南粮仓到塞上边陲,又从滨海产盐之地到缺盐的穷乡僻壤,万里跋涉,奔走于途,扩大着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徽商积累壮大着民间财富,令南国城镇变为商业辐辏之地,为现代化作了必要的铺垫,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文化中心由中原向东南的转移。
除了地域和经济势力,商人之所以能够结成商帮,还在于经营的信条、商业文化的认同。
敢于闯荡,善于交游,专于事业,精于算计……商人的必备特质,都出现在晋商和徽商身上。在经商过程中,又衍生出不少礼数、帮规、章程以及传统。“以义保利”“合义为利”的商业伦理与原则,都受到晋商和徽商的重视。
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是一部光荣史,也是一部血泪史。
顺治初年,范永斗等八家晋商,因助力清军有功,被赏以“皇商”特权。康熙平定准噶尔部,范氏皇商奉旨输送粮饷,办事极为得力,受到皇帝嘉许。至雍正时,范氏家中已经有了二品官员。
然而到乾隆时,范家的事业渐渐不中用了。乾隆几次下江南,耗费极大,国库亟需填补,于是打上了巨富之家的主意。范氏被寻找罪名,清产抄家。红极一时的范氏皇商事业,以喜剧始,以悲剧终。
徽商同样也是皇家和权贵勒索的对象,凡朝廷大典、工程赈灾乃至筹边兵饷,无不需盐商捐输报效。康乾二帝十二次下江南,徽商大把大把花钱的豪举,点缀着“康乾盛世”的辉煌景观,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多获得几张盐引,却往往招致破产的结局。
哪怕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免不了遭遇敲诈勒索,当面临外商排挤、派系打击,及至被革职抄家时,朝廷上下却没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中国古代官与商的畸形关系,为商人的命运平添了注定式的悲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临近结局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晚年的乔致庸,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发表了一段内心的独白:
“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
“现在呢?一个老地主坐在这个大院子里。一个老地主,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你把我的一生都毁了,你还救国,还救民,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乔致庸的独白,交织着深情、悔恨和痛苦,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像是对商人这个特别阶层的宿命的拷问。
如果乔致庸不是临危受命,弃文从商,接手家族生意,他会一直做个读书人。
徽商素有儒商之称,只要条件允许,就会要求家中子弟参加科举;而一般认为,晋商不特别看重功名,连皇帝都曾抱怨山西人有钱,但不重视科举取士。
不过,在乔致庸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儒商的光辉。
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晋商供奉关公,徽商供奉朱熹。而在乔家大院里,乔致庸也会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屏门上,作为治家的准则、儿孙启蒙的必读课。
乔致庸可以“汇通天下”,却无法“按照自己的路走”,以一个“老地主”的身份,终了此生。
同样弃文从商的汪定贵,最后拿钱捐了个官,但那时他最在意的,却是为商人出口气。
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些在我们看来富甲一方、无比成功的商人,却苦于命运的逼迫,无力挣脱。在现实和理想的交织中,何处才是归属?
千百年历史里的商人,在生存斗争中,要么甘居末流,在矮檐下忍辱求活;要么依附权贵,成为官方附庸,甚至变成官商皇商。
今天的商人,身份地位和经营环境,跟当年相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晋商与徽商仍然会时时被人提起。个中缘由,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财富光环,还在于他们的进取、信义、理想,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
一个商人,该被如何铭记?
是胡雪岩的传奇,是乔致庸的信义,还是汪定贵讳莫如深的志向?传统商帮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商业正在对社会发挥更具主导性的力量。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商人通常都是最先嗅到时代气息的人,社会时常有赖于他们的开拓与坚守。
当晋商与徽商已成往事,他们的故事,我们仍会一提再提。我们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潮流里,谁在突围,谁被湮没,也将成为后来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