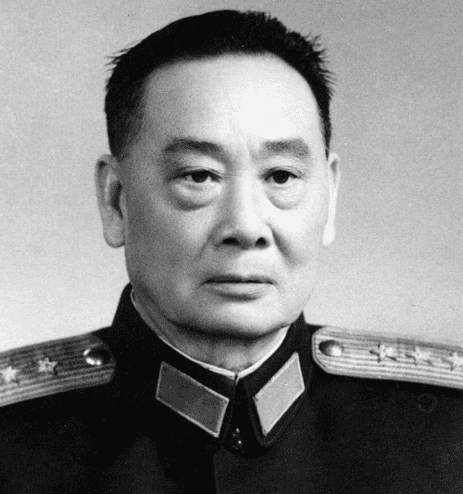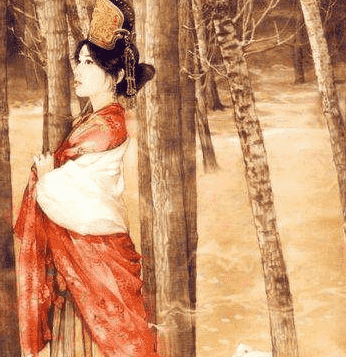“自己的”明清时代皖南佃仆奴仆辨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的《明清时代皖南佃仆奴仆辨》,希望大家喜欢。

魏金玉
微信版第1205期
内容提要:作者根据明清徽州文书资料,考辨出明清时代皖南地区的佃仆和奴仆之间的区别:佃仆是土地房产的附属物,而奴仆或奴婢是主人所完全占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前者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经营和生活;后者没有自己的经济,听从役使,衣食于主人。
明清时代皖南地区的佃仆和奴仆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佃仆是土地房产的附属物,而奴仆或奴婢是主人所完全占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前者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经营和生活;后者没有自己的经济,听从役使,衣食于主人。但是,他们同主人之间都存在着严格的隶属关系,世代相承,人身是不自由的,所以,同被称为世仆。因此,有研究者根据这后一点认为佃仆就是奴仆或奴婢,没有什么区别。就这后一点而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自由的程度,亦即占有是完全的或者是不完全的。这是需要认真分辨的。不过,我无能对完全占有和不完全占有给以明确的界定,并联系实际,全面地详细论证,只能根据一些具体事例试作说明。
事例一:明嘉靖二十年(1541)佃仆吴保将长男社天出卖给房东汪安。吴保是汪安的佃仆。这需要作点说明。我们在嘉靖《休宁汪姓誊契簿》中看到,吴保本来是汪法的佃仆。嘉靖十四年(1535)汪法将自己占有的火佃屋地份额、亦即佃仆屋地的一部分,出卖给汪三太。另外的部分还在别人的手里。当时,佃仆多半是多个所有者共同占有的土地房产的附属物,隶属于众多的主人,这是需要事先交代清楚的。汪法只是这块火佃屋地的众多主人之一。有关卖契如下:
十二都住人汪法,今来缺少银两物用,自情愿凭中将二保首字六百廿八号火儿房屋五间、厨下屋并鱼塘,弟兄三分中取汪法边合得分数内,取火儿屋地二厘五毛,上至滴瓦,下至地脚,四围俱全板壁,尽行立契出卖与东北隅三图汪三太名下,三面议时值价白纹银三两三钱正。其价当日收足,其房屋火儿地尽行出卖与人,买人随即管业。未卖之先,即无重复交易,及内外人占拦,并是汪法之当,不及买人之事。其税粮候造册之年,听自到本户起割税粮,户内人等即无阻挡。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出卖文契为照。
住火佃人邵月、邵真、邵贵、吴保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出卖人 汪法
中见人 汪岩
次年,汪三太又将这份火儿地转让给汪安。汪三太出具了如下的一张领约:
休宁县东北隅三图汪三太今立收领到十二都一图原买汪法嘉靖十四年将火儿地原卖本家,今自退还同户汪安等。价尽行收讫,契文随即交付。所有汪法前后卖坟山并余山等契文,日后索出不行用。今恐人心无凭,立此收领为照。
嘉靖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立领人 汪三大
依口代笔人 汪 乙
我们知道,明清时代佃仆是土地房产的附属物,他们是随同土地房产的买卖转让而更换主人的。这里吴保就是随同当地鱼鳞册上首字六百廿八号的土地房屋,由汪法出卖给汪三太,汪三太转让给汪安的。汪法出卖的这块火儿屋地的面积虽小,却也随带有它的附属物-佃仆。后一张契约中的“契文随即交付”,指的是嘉靖十四年汪法所立的卖契,现在由汪三太交付给了新买主-汪法的同族汪安。所以,嘉靖十四年汪安的卖契才被标明是“来脚契”,收在这本誊契簿里。正因为有了这张来脚契,汪三太才不立卖契而写了一张领字,说明收到了地价,随同这张来脚契交给了新买主-汪安。这可能是原卖契尚未过户,新买主可以持之办理过户手续,因而可以省却再立一张新卖契的缘故。所谓“退还同户汪安”,意思是说,汪安是原来卖主汪法的同族,土地房产卖给汪安等于退还给了汪家。吴保作为土地房产的附属物,也因此而随同这份火儿屋地回到了汪家。在这一买卖转让过程中,吴保在契约上和实际生活中都不曾与鱼鳞册上登记的编号首字六百二十八号的土地房产相脱离。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确认,吴保是汪家的佃仆。
嘉靖二十年吴保因交不出田租,将长男社天出卖给汪安,立下了如下的一张契约:
十二都住人吴保,今因缺少田租无措,自情愿将长男社天,年方十岁,凭亲人邵星为媒,着与房东汪安名下,接受礼财银三两二钱正。其银前去了还田租银两,男随即造门听从训诲,长大与男婚娶,终身奉养工活,无得懒堕东西走躲等因。如有此等,父行跟寻送还,即不敢违误。所卖其男两相情愿,故非相逼,亦无私债退除。今从过门之后,一听房东使唤,日后无得回宗。如违,经公理治。倘有风烛不常,天之命也。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出卖婚书为证。
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二日
立婚书人 吴保
依口代笔媒人 邵星
试比较一下嘉靖十四年与嘉靖二十年这两张契约,就可以发现:出卖佃仆屋地的契约是地主出具的,而出卖佃仆子孙的契约是佃仆自己出具的;前者说明出卖的对象土地房产的位置和面积,以及登记在当地鱼鳞册上的编号,后者不涉及土地房产,所以不提及佃仆所附属的土地房产,却必须说明被出卖者的姓名、性别和出生年月或年龄;前者是出具给购买者的,与附属在土地上的佃仆无关,后者是出具给佃仆的家主的,因为购买者是佃仆的主人,出卖者必须提到购买者是自己的家主。一般说来,前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之间,后者只可能发生在佃仆与其家主之间。换句话说,在佃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佃仆只能将其子孙出卖给家主,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无需乎说明,佃仆将自己的子孙出卖给自己的家主,当然是得到了家主们的许可和同意的,没有家主们的许可和同意,佃仆自己是不能出卖自己的子孙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地主与佃仆之间的严格隶属关系下,佃仆无权处置自己一家的人身,不能出卖自己和子孙的人身给家主以外的任何人,但却可以将自己的子孙出卖给自己的家主、或众家主中的某个人。看起来,这一点特别突出,家主需要通过购买,才能将自己所占有的土地房产的附属物佃仆中的某个人转化为自己的奴仆或奴婢,不通过这种购买,家主还不能将自己的佃仆转化为自己的奴仆。在这里,所谓地主的超经济强制似乎也难以为力,不能随意将隶属于自己的佃仆强制转化为自己的奴仆或奴婢。地主要想将隶属于自己的佃仆转化为自己的奴仆或奴婢,还得通过买卖的交易手续和过程,这是因为佃仆与奴仆或奴婢的处境和身份不同、不能混淆的缘故。
上面抄录的嘉靖二十年吴保出卖吴社天的契约就是这一转化的凭证。这里,在家主的许可和同意下,佃仆吴保可以出具出卖儿子的契约,也可以接受出卖儿子的代价。看起来,佃仆的这两项权利,还是家主所不干涉的。这就意味着佃仆对于自己一家人的人身还是享有一定权利的,换句话说,家主对佃仆一家人的人身占有权是不完全的,与对奴仆的完全占有和奴仆完全无权处置自身及家人的人身是大不相同的。
为了说明上述契约就是这一转化的凭证,下面再列举两个同类的事例。
事例二:胡音十出卖儿子胡懒囝。胡音十出具的卖契像吴保的卖契一样,都称为婚书。这是因为明清时代的社会虽不禁止,却也并不鼓励民间存养奴婢和买卖人口,民间就把这类买卖奴婢人口的契约,不管买卖的是男是女,讳言为婚书,这其实是当时官私上下都心照不宣的事实。胡音十出具的婚书如下:
立卖婚书十二都住人胡音十,今因缺食,夫妇商议,自情愿将男胡懒囝乳名昭法,命系辛丑年三月十五日申时,凭媒说中出卖与家主汪囗囗名下为仆。三面议作财礼银叁两五钱正。其银当日收足,其男成人日后,听从家主婚配,永远子孙听家主呼唤使用,不得生心变异。如有等情,听从家主呈公理治。恐后无凭,立此卖男婚书存照。
长命富贵,婚书大吉。
嘉靖三十年二月三十日
立婚书人 胡音十
媒人 胡永道
中见人 汪玄寿
事例三:王连顺出卖儿子王得金。契约如下:
立婚书仆人王连顺,为母死棺木后事无处设法,将子得金,本命生于嘉靖甲寅十一月十日卯时,今年一十七岁,写立婚书卖在汪镇东家主名下,当时得受身价银七两正。自卖之后,听凭家主唤使,子孙婚配俱照向来村例,尽由家主,不得违拗以及推故逃避。如有前件情事,一听家主呈公究处。恐口无凭,写立婚书,永远存照。
隆庆四年六月奉书男 王得金
立婚书仆人 王连顺
凭家主 汪允升朝奉
妻舅 程乞
试把上面抄录的三张婚书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佃仆向家主出具的卖子文书。佃仆是卖方,家主是买方,佃仆一方收受出卖的代价,并交出自己的儿子给家主作奴仆,家主一方付出代价,并接收佃仆出卖的儿子作为奴仆。通过这一买卖的手续和过程,佃仆的家人转化成了家主的奴仆。这些婚书都是佃仆子孙转化为家主奴仆的凭证。这后一点需要作一点说明。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是契约中说明了被出卖者的姓名、性别和生年岁月,明确了出卖的对象,而且是契约中明确规定了被出卖者到家主家中所应接受的约束。这些约束是:“男随造门听从训诲,长大与男婚娶,终身奉养工活,无得懒堕、东西走躲等因。如有此等,父行跟寻送还,即不敢违误。所卖其男,两相情愿,故非相逼,亦无私债退除。今从过门之后,一听房东使唤,日后无得回宗,如违经公理治。倘有风烛不常,天之命也。”“其男成人,日后听从家主婚配,永远子孙听家主呼唤使用,不得生心异变,如有等情,听从家主呈公理治。”“自卖之后,听凭家主使唤,子孙婚配俱照向来村例,尽由家主,不得违拗,以及推故逃避。如有前件情事,一听家主呈公究处。”
综合起来,这些约束包括如下几点,这几点应该说就是佃仆转化为奴仆或奴婢的证明:第一,出卖之后,被出卖者就要到购买者,亦即家主家里生活。此前,他虽有佃仆身份,却是不能到家主家里生活的。
第二,他到家主家里生活是为了听从训诲、奉养工活、听凭使唤的。此前,作为佃仆,虽然也要为家主服役,但那是有限度的,有一定的范围和数量界限,除此以外,他还要佃田种山,一般主要是佃田种山。现在,服役成了专职,变成无边无涯、毫无限度、随时可以使唤的了。同时,劳动者也同自家的佃田种山的经营活动分离开了,佃仆转化成为了脱离自家经营的单纯的奴仆。这时主人如果要役使他种地种山,那也是为主家干活,与佃仆自己家里的经营无关了。
第三,奴仆的身份是终生的,世代相承。这就是所谓终身奉养工活、日后无得回宗、子孙永远听家主使唤的意思。此前,作为佃仆,其身份也是终生的,世代相承。二者并无不同。这一点并未因劳动者由佃仆转化为奴仆而有所改变。但是,终生的处境、活动和身份地位,在佃仆和奴仆之间是并不相同的,虽然他们同家主中间同样存在着严格的隶属关系。
第四,佃仆转化为奴仆以后,人身完全为家主所占有,婚配就全由家主一方决定了。此前,作为地主佃仆的男性或女性,人身并未完全为家主所占有,他们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佃仆转化为奴仆或奴婢之后,婚配全由家主,对自己的婚姻,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了。
第五,这些劳动者被出卖以后,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到家主家里以后,劳动者的佃仆家长对劳动者的行为仍然负有连带责任。如果,劳动者有违背契约规定的行为,家主认为有必要经公理治,佃仆家就要等着吃官司了。契约中的经公理治,意思是说,家主可以向官府和地方里甲保甲以及宗族祠堂等等控告劳动者,要求对他们违反契约规定的行为给以惩治,惩治的对象不只是劳动者本人,还包括有劳动者的家长。
这最后一点,可以通过以下事例说明。
事例四:佃仆冯初保将次男冯德儿出卖给房东谢 以后,还要承担冯德儿逃跑的责任,在房东的要挟下,交还原来收受的财礼。为了交还这笔财礼,冯初保出具了如下一张契约给谢敦本堂。
西都冯初保将次男冯德儿过房与房东谢綵以为家仆,抚养成人,於上年背主逃出,於今年正月内带妻子回家,是房东社右状投本都六甲里长谢香处,取讨原礼银物,德无措处,凭父初保托叔贞保,自情愿凂求敦本堂房东谢纷、谢纹、谢锺三大房,出备礼银,付还社右。其次男德儿妻子,及日后子孙永远应主,无违敦本堂三大房子孙使唤,不敢抵拒。今恐无凭,立此文约为照。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立文约仆人 冯初保
同男 冯德儿
依口代笔中见堂叔 冯贞保
冯初保出具了这张契约之后,冯德儿的原家主,亦即谢 家,也出具了一张契约如下:
西都谢镗,原父用过礼银讨到本都火佃冯初保次男名唤德儿,在家抚养成人,后冯德儿逃走碗窑,於本年正月回家。思伊逆主,身行告理。是冯初保无从措处赎身银两,今冯初保投借到谢敦本堂三大房出备赎身银正。其银收讫,其冯德儿妻子听自谢敦本堂三大房子孙永远应主使唤,本身即无异言。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再批所有原主婚书随即交付。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立婚约人 谢镗
中见人 冯贞保
在这一事例中,冯家是谢家的佃仆。冯初保将冯德儿出卖给谢 以后,冯德儿出逃,冯初保还要承担责任。作为佃仆,冯家的人是谢家土地房产的附属物,不能离开土地房产而自由移动,如果有成员擅自离开,佃仆家是负有责任把他追回的。现在,冯德儿虽然被卖给谢家作了奴仆,并没有摆脱原来的佃仆身份。冯德儿逃离之后,再回家来,被地主谢家发现,谢家就向里长控告,要求冯初保家还人,冯家不能拒绝,也不敢拒绝。这里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谢家要求冯家为冯德儿赎身,亦即退还出卖时接收的财礼。冯家没有退还财礼的能力,为此,冯初保不得不向谢敦本堂三大房筹借这一笔赎身银两,代价是冯德儿到谢敦本堂三大房名下为奴作仆。这实质上是将冯德儿转卖给了谢敦本堂三大房。但事实上,这时的冯德儿是谢家买来的奴仆,佃仆冯初保无权转让自己原先已经卖出的儿子,也不能接受这一转让的代价。所以,上录冯初保出具的文约,不是婚约,不具有买卖契约的性质。作为佃仆家长,出具的这张契约只起着保证这一转让的作用。显然,冯家的这一举措是事先得到了谢家同意的,谢家不同意冯家是不能作出这一保证的,更不用说什么转让了。只有谢家才有资格转让自家的奴仆,出具有关契约。所以,谢 的儿子谢镗就按照惯例出具了一张婚约,声明收到了冯德儿的赎身银两,今后,冯德儿妻子听自谢敦本堂三大房子孙永远使唤。同时,将原来的婚书随即交付给新的卖主-谢敦本堂三大房。这样一来,谢家收钱交人,算是正式完成了这一买卖转让奴仆的手续。
必须再次强调指出,这一买卖转让没有超出佃仆众多主人的范围。谢镗和谢敦本堂三大房都是佃仆冯家的有份主人。只有在佃仆的众多有份主人中间,才能实现佃仆家成员的买卖和转让。超出这一范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房屋买卖转让其附属物佃仆,而不能将佃仆剥离土地房产单独买卖转让。
这一事例,是以赎身借贷为名,行买卖转让之实,被出卖的劳动者并没有赎身摆脱奴仆的身份回到自己的佃仆家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出卖的佃仆子孙不能赎身,不能摆脱奴仆的身份。在获得家主许可的条件下,他们是可以赎身,摆脱奴仆的身份,离开主家,回到自己的佃仆家里的,不过,这时他仍然是主家的佃仆。例如:
事例五:叶进德回赎自己出卖给家主的儿子。有关契约如下:
立还文书人叶进德,原于万历年间,将长男应祥卖与房主程名下,为义男使唤。今因妻死,身老无人伏侍,愿将财礼取赎回宗。向蒙恩主扶养成人,无恩可报,议定递年着应祥应役五工。倘主呼唤,不致抵拒。立此文书为照。
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立还文书人 叶进德
中见房东 程斯善
程良发
依口代笔人 汪 义
叶进德称程姓为房主,自称立还文书人,可见他是程家的佃仆无疑。他是以佃仆家长的身份出具这张契约的。所谓将财礼取赎回宗,就是将原来出卖儿子的代价退还房主,为儿子赎身,让儿子离开房主家,回到自己的佃仆家里生活。不过,这里还有附加的条件,这就是此后应祥每年应服役五工。应该说明,不论应祥是否承担这每年的五个工,他仍然是主家的佃仆。他的奴仆身份可因回赎而摆脱,他的佃仆身份却是不曾摆脱的。
佃仆可以将自己的子孙出卖给家主,也可以将自己的子孙典当给家主。
事例六:胡家是洪家的佃仆。胡家第五代胡喜孙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胡社隆,次子胡社禄,万历十四年胡喜孙要为长子胡社隆娶妻成家,因为没有钱作财礼,不得已,把二儿子胡社禄出当给洪家祠堂作奴仆,换得了一两七钱银子,算是解决了问题。为此,胡喜孙出具了一张当子文书给洪家祠堂。
五都仆人胡喜孙,今为娶长媳缺少财礼,自情将二男胡社禄当到房东洪寿公祠,纹银一两七钱正,其银,照例每月加利贰分算,约至来年八月间,将本利一并送还,不致少欠。今恐无凭,立此当约为照。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
立当约人 胡喜孙
依口代笔 洪天南
中见人 洪德聚
胡喜孙典当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得到了一两七钱银子,这一两七钱银子是要付利息的,利息相当苛重,每月二分行息,一两七钱本银,一年应付利息就是四钱零五厘。契约中规定“来年八月间将本利一并送还”,对胡喜孙说,这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一直拖到万历三十四年,胡社禄被当在洪家祠堂为奴作仆二十年后,胡家依然无力清偿这笔债务。这时,债务本息已经滚算到八两一钱六分,是当初一两七钱银子的四点八倍了。这年,洪家祠堂忽然要算帐收债。算帐结果,胡社禄二十年为奴作仆所支出的劳动毫无代价。这还不算完结,胡家还要付出现银一两七钱,另以胡家所有的粪草田作价贰两五钱一分交给洪家祠堂,下欠三两九钱五分,洪家祠堂说是“姑饶不计”。这才算结清了债务。胡社禄才得以离开洪家祠堂,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时,他已不再是洪家祠堂的奴仆,而只是洪家的佃仆了。在这一全过程中,胡喜孙承担了出当和回赎的全部权利和责任。
佃仆不只可以出当自己的儿子给家主,还可以出当自己的女儿给家主。
事例七:程爱孙将自己的女儿出当给家主,出具了以下一张契约:
立当约人程爱孙及妻,今因欠缺日食,自情愿将亲生女名唤末弟,本命系于乙亥年二月廿七日吉时生。今凭家主出当到家主正发朝奉名下,本纹银贰两正。其银递年秋收谷之日硬交谷四砠送至门上,不得囗囗。恐口无凭,立此当约存照。
仝年四月廿四日又当去本纹银五钱正,凭胡之际 递年硬交谷乙砠作利。
康熙三十七年三有廿七日
立当约人 程爱孙
代书家主 胡社德
程爱孙将女儿出当给家主之一-正发朝奉,一共得到贰两五钱银子。这银子是有利息的,但是,利息不是交纳银子,而是每年共交谷五彧。至于程爱孙日后是否赎回了女儿,我们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出当人,接受代价的人,和承担偿付每年利息的人,都是程爱孙一人。他像上例中的胡喜孙一样,承担了出当的全部权利和责任。
当然,佃仆出当自己儿女,像出卖自己的儿女一样,是得到了家主们的同意的,家主们不同意,佃仆自己是无权擅自决定出当和出卖自己的儿女的。所以,像我们一再所强调的,佃仆出当和出卖自己儿女的交易只能出现在佃仆与佃仆的家主之间,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事例八:另外,我们还见有这样的事例,作为族产附属物的佃仆,在取得全族地主们的同意以后,入赘族内一户地主家的婢女,充当年限婢婿,为这户地主特别劳动22年。在此期间,他具有了两重身份,既是地主全族的佃仆,又是这户地主的婢婿。虽然22年工满之后,劳动者可以夫妇离开这户地主家门,终结年限婢婿的身份,他们如有子女,却要留一个给这户地主作奴婢。我们把有关的契约照录如下:
安山代招亲婚书,房东谢良善、谢用明等,今有庄仆汪有寿,自幼父母继亡,次弟逃散,三弟众卖樟村度活。今有寿孓立,日食难度,飘零无倚,向在外境佣工糊口。房屋倾颓,二门主众商议,久巳拆毁,身无所栖。且年登二旬有五,无力婚娶,若不代为招亲,汪仆一脉恐淹没矣。今有本族谢正仁家有使女,是有寿凂求二门房东主婚,前往招到房东谢正仁使女为妻,议定填工二十二年,以准婚娶财礼之资。工满听自夫妇回宗。日后生育,无问男女,听留一赔娘。所有二门主众当受酒礼银讫。二门人众每房议一二人画押为凭。余外房东家不齐,不得生端异说。今恐无凭,立此招亲婚书为照。
再批二门婚姻丧祭照旧应付无词,众批。
崇祯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立代招亲婚书 谢孟礼、谢正宗、谢正修等十五人
十几年后,22年的年限未满,汪有寿的妻子死了,这时汪有寿要求妻主将另一个婢女给他为妻,所以,在这张契约后面,还有以下一段批语:
顺治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有寿因前妻富贵不幸先年病故,思以失配无力再娶,托凭二门主众复凂求妻主将使女联喜另招为妻。所有财礼无措,众议著寿身照旧外,填工拾年,以准复招财礼。日后生育男女,听妻主使唤,二门无得异言。此照。众批。(注: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看来,这个汪有寿,当时并未租种家主的土地山场,所居住的房屋,也早已拆毁。他丧失了自己的经济,但他仍然是家主的庄仆,并没有获得自由的身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可以一再选择充当年限婢婿的前途,与毫无婚姻自主权的奴仆不同。年限满了,他还可以回到自己的佃仆家里,不过,他的子女却没有这么幸运,按照契约规定,或多或少,总要留一个在主家听从使唤,被留在主家的,就不能摆脱奴仆的命运。同时,汪有寿在充当年限婢婿的几十年中,他仍然是众家主的庄仆。“二门婚姻丧祭照旧应付。”
最后,我们抄录一张清代康熙年间的契约,用以表明上面揭示的事实,进入清代以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事例九:姚季恩的卖子文书:
立卖婚书人姚季恩,今因母病,缺少衣衾棺材使用,自情愿将亲生长男名七十,命系丙申年二月十二日生,凂媒出卖与长房家主名下为义男,三面议定时值礼银五两五钱正。其银当日收足,其男随即过门更名使唤。其银并无短少准价,亦无重复交易。倘有走失异说,俱系卖人理直,不涉买主之事。倘有天行时气不测等情,乃天命也。今恐无凭,立此婚书永远为照。
康熙元年九月 日立
卖婚书人 姚季恩
凭媒 洪夏夷 汪登名 郑高
代笔 许六育
总起来看,作为佃仆,主人可以随同土地房屋买卖转他们,佃仆自己是不能离开主人的土地房屋的,不能自由处置自己一家人的人身。但在这众多主人中间,佃仆却可以选择出卖典当自己家人给某一主人的转让行为,有条件地处置自己家人的人身。同时,他还保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这就是佃仆所具有的、与奴仆或奴婢不同的权利,他们的人身并不是主人所完全占有的。不过,这时他仍然是主人所占有的土地房屋的附属物。
这就是明清时代皖南的佃仆和奴仆或奴婢,在与主人的严格隶属关系方面的区别。了解这一区别,可能有助于对前此有关社会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对完全占有和不完全占有的认识。这个说明虽然免不了有许多缺点,但如果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话,应该就在这里。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