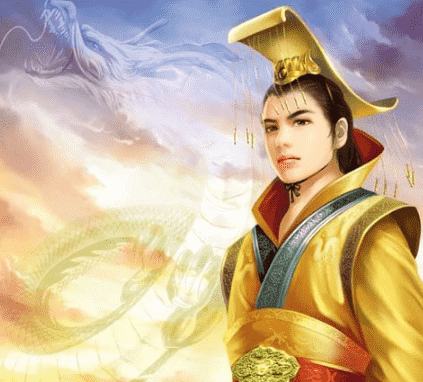“士人”从古至今来看,“隐”分为几种?元朝士人对仕和隐抉择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知识巨轮的《从古至今来看,“隐”分为几种?元朝士人对仕和隐抉择》,希望大家喜欢。

仕与隐的选择,是中国传统士人要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承平年代,士人们面临的是想仕却怀才不遇的愤懑,欲隐而壮志难酬的不甘,但无论作何选择,都只关乎个人的前途境遇。
处于朝代更迭之际的士人则与此不同,他们身为前朝遗民,一方面有难以忘怀的故国之思,另一方面又有经世济民的个人理想,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仕与隐。
除此之外,社会道德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忠君”思想成为横亘在仕隐之间的障碍,也成为束缚个人选择的枷锁。
由宋入元的士人在面临以上境遇的同时,还要面临由于政治地位下降所带来的物质贫困,这也成为了他们徘徊在仕隐之间的一重关卡。而最终做出仕元选择的仕元词人则注定要经历远超他人的矛盾与挣扎。
艰难:元初南人的生存与仕进
在分析仕元词人的仕隐心态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元朝统治之下江南士人的生存境遇与仕进情况,这主要与元代所实行的科举制度、儒户制度,以及在复科之前官员的仕进途径有关。
有元以来,科举制度废而立,立而废,始终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自至元十六年元世祖统一中国以来,元朝有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未曾实行科举,直到皇庆二年,元仁宗才下诏恢复。延祐元年,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举行会试和殿试。
此时距离宋亡已经35年,许多经历过世变的士人或已年近花甲古稀,或早已下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蹉跎殆尽。
宋亡之时,仕元词人的年龄多在20与40之间,处于少壮年时期,而延祐复科之时,年龄最大的赵文已经76岁,在恢复科举的第二年便与世长辞,年龄最小的陈恕可也已经57岁。
其他生卒年不详的词人也大抵与他们相差无几。科举作为古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进阶之途,其兴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科举的废除一方面使士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资本,生活日益贫困,不得不转从他业;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精神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怀疑。
科举废除之后,时文成屠龙之技,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之人也因为它于世无补而弃之不学,甚至不知为何物,这对那些以科举为业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摧毁。还有的人一生对科举念念不忘,以至于成终身之恨。刘壎在写给乡贤曾月崖的墓表中记述了他对科举的执念:
“大德甲辰岁,年六十有九······吾故曰可哀也。”
曾月崖也曾出任儒学教授,但这并不能弥补未能科举给他带来的遗憾,以至于在临终之前依然愤懑不平。
赵文、吴澄等人平日对于科举多有鄙薄,赵文称其为“隋唐弊法”,认为“科举累人”,使得士人为功名所役,既无读书之闲,又无养亲之乐;吴澄年十六即厌科举之业,认为科举所取不过辞章之虚,更使“举世浸淫于利诱,士学大坏”。
这其实只是对于宋代科举偏重辞章的不满以及无可奈何的慰己慰人而已。一旦科举恢复,或“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或承担阅卷之责,“闻命就道,略无辞避”,为儒科有人而欢喜不禁。
像赵文这样不顾老迈依然参加科举的士人还有很多,胡助《和马伯庸同知贡举试院记事》有句曰:
“宗公群彦列如墙,半是先朝白发郎。”
可见科举恢复以后,不少士人虽已入迟暮之年,仍然跃跃欲试,希望完成年少时的理想。他们对于科举的热情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兴替而湮灭,反而因为暂时的中断而日益高涨。
由此可以推知,元代初期科举的废除加重了宋末士人因民族入侵、国家颠覆所产生的不满,入元前后的地位落差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怀念故国,从而拒绝与新统治者合作,这大概也是南宋遗民众多的原因之一。
儒户制度的设立及影响
儒户是元代法定的诸色户计中的一种,元代的户计按照职业划分,例如民户、军户、僧户、道户等等,每一种户计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儒户制度早在蒙古灭宋之前就已确立,南宋灭亡之后,江南士人也被逐步纳入儒户之列。原来汉地的士人入儒籍需要经过专门的考试,江南儒籍的设立则较为宽松,“仅根据坊里正等人的攒报,凡是旧宋的‘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皆可入籍”。
但因标准过于宽松,也就出现了不少人冒入儒籍的现象。关于儒户的权利和义务,萧启庆在《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此处仅简要概括。
儒户的义务根据学历和年龄划分有两种:
一种是学,年轻儒生需要坐斋读书,中年儒生则仅须供月课;
另一种是教,主要针对在宋代已获得功名的硕学耆儒,需要在每月朔望给学生上课。儒户的权利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奖学金性质的补给,另一方面是可以免除部分赋役。
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入户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保障。首先是赠给的发放并未制度化,不仅标准不一,还存在被人冒领和克扣的现象。
“体知建康儒学并上元、江宁县学,及明道、南轩两书院,除学官外,名儒耆宿月支学粮,养赡不一,每名一石者,有五斗者,有一名两处支粮者,有一家数口共食行供饮膳者,有不系贫寒之士,冒滥支请者”,九江大儒黄泽初“月致米六斛、钞三十千”,此后则“月廪削其三之二”。
其次,在籍儒户虽然可以免除部分赋役,但是地税、商税并不能豁免,差役也只能儒士本身可以免除,并且这项特权在大德后期一度取消。
由此可见,儒户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人的经济水平,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士人的遭遇仅仅是没有变得更坏,而完全不能和宋亡之前相比。
在失去了科举这一进身之资后,士人们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资本,政府的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另外,儒户制度除了缓解经济压力之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
仕进之途:由儒与由吏
姚燧《送李茂卿序》说:
“大凡今仕唯三途,一由宿卫······郡、县,十九有半焉。”
如上所述,在科举恢复以前,元代的仕进之途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
一类是看“根脚”,只有家世显赫的蒙元贵族才能够充当宿卫,逐步晋升,并垄断绝大部分上层职位;
一类是由吏进,地方上会定期向中央提供考试合格的儒生充任胥吏,称为“岁供”;最后一类则是出任学官。元初士人若想出仕,基本只能通过后两种途径。
元代的吏比之唐宋地位有所提升:
“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越十数年,吏习丕变”。
因部分人不能修洁自守而逐渐相熏相染,以至于“通天下皆然,莫可救药”,到了元仁宗时期,又再次恢复到了“贵儒抑吏”的状态。
并且下层胥吏的任务极其繁重,“日劳形于案牍,随群随队,役役焉习奴隶书之不暇”,这并不符合“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
所以,大多士人在“舍儒就吏”之时往往会犹豫再三,“屈身为吏”说到底是儒士的一种悲哀。和充任胥吏一样,出任学官往往也是一种出于无奈的选择。刘将孙诗曰:“二十年无进士科,新愁旧学久消磨。一官乞与闲无奈,徙倚庭前自放歌。”
正是大多数儒官的心灵写照。首先,讲学授书并不是士大夫的真正理想,只是在士人地位下降情况下所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权宜之策。
吴澄《送邓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说:
“并诗世以儒为无用久矣,惟譔述编纂之职、讲论传授之事不得不归之儒,是所谓无用之用者。”
其次,元代儒士众多,而相应的职位却只有那么几个,僧多粥少,竞争压力很大。
“年来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员无穷而阙有限,于是枢机日趋于密,始仕须府与州,再调乃得路学。”
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当权者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需要从基层做起之外,还有须先到边远之地巡检,驱驰弓马缉奸捕盗这样的无理要求。
即便如此,一旦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是有众多儒士趋之纷纷,不辞劳苦。
除此之外,学官的晋升通道也格外狭窄。“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余年,比及入流,已及致仕”,也就是说,从普通教官升为教授,基本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萧启庆先生所说,“无论是以吏进还是以学官进,大多数的士人都必须永沉下僚,位居人下。这是元代士人沮伤的主要原因。”
科举废除,选官之途狭窄,士大夫的理想被搁置,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这一切都加重了江南士人对于新朝统治者的不满。
一方面,他们碍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在现有的仕进之途中挣扎前行;另一方面,现实中所遭遇的劫难又使得他们更加怀念故国,怀念宋亡以前士大夫的辉煌时刻。
所以仕元而恋宋这种群体心态的产生,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仕元词人正好生活于这一时代,他们中除了个别人在朝堂身居高位以外,其他皆碌碌下尘,正是这一类群体的代表。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