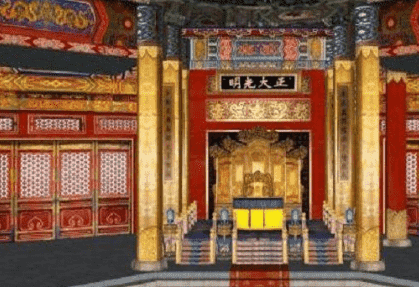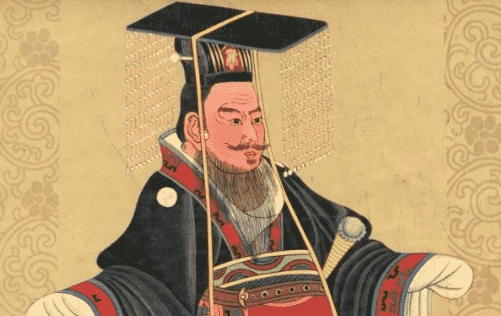开国中将皮定均是怎么去世的?妻子怀疑他被暗杀
皮定均,中将。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年7月7日在军事演习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生如闪电之耀亮,逝如流星之倏忽。一代将星在参加演习的途中,座机与山峰相撞。夫人张烽亲自为丈夫撰下碑文。
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有关省级报纸,突然把皮定均将军的照片镶上了黑框。东南天空一颗明亮的将星殒落了。皮定均是为了去参加东山岛三军军事演习,座机撞山而遇难的。
清晨,边散步边听新闻的皮定均突然喊大儿子皮国宏:“快回家让你妈妈打开收音机,朱老总去世了!”这天的早餐一家人吃得很沉闷,大儿子国宏为父亲的安全担心,说:“爸爸,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一是可以学习,二是我可以助你的警卫员小刘一臂之力。”

7月7日上午9时29分,皮定均乘伊尔-14从福州起飞,10点33分,到漳州机场,15分钟后,换乘米-8飞机去东山。
11点15分,将军在这一瞬间,化作了闽东山峰上的一声惊雷。
夫人张烽表现得镇定自若,她把丧事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人后,却止不住每每潸然泪下。
皮定均牺牲一年后,骨灰送往北京八宝山。15年后,应豫西老根据地群众的要求,部分骨灰安放在登封革命烈士陵园,另一部分,按照张烽的愿望,存放在毁机的灶山之巅。张烽别无他求,只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和长子一起相伴在云霞缭绕的灶山之上。
她托人从惠安石雕场购得一块上等雪青石墓碑,亲自撰下碑文:
九死一生,将军闯过枪林弹雨,永留百世英名
人妖颠倒,亲人竟遭机毁人亡,谁解千古之谜
事隔多年,张烽回忆起丈夫的死,说:“有一次,他到医院探望一位患偏瘫的战友,回到家时对我说:‘我将来要是得了那种病,你给我点安眠药。我可不那样活着受罪。’我说,‘你不会得那样的病,你呀,要死,也就是一倒下就死了。’这话却应验了。”
那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我很希望有一个我喜欢的爱人。我很愿意得到爱情。我很愿意爱一个人。我很愿意得到一个爱我的人给我的爱情。可是我不会说,我不会说,不敢说,说出来以后怕她不跟我,不爱我,这怎么办?”
1940年8月的一天,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正和涉县县长郑晶华研究工作,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姑娘。她十七八岁,中等个儿,瓜子脸儿,一双特别有神的眼睛。眼神里含着漂亮姑娘常有的拒小伙子于千里之外的厉害。皮定均心中的情弦,竟然一下子就被拨动了。姑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向县长汇报完工作,转身就飘走了。她不是不知道县长屋子里还有一个大活人,但是她一点也不好奇,她根本就不打算对一个军人感兴趣。
“哎,这是谁呀?”
“我们县的妇救会主任。”
“呃——怎么过去没见过?”
县长对这种微妙态度的流露是很敏感的,笑了。
“她叫什么名字?”

“张烽。”
“哪里人?”
“城关的。”
“多大了?”
“十七八岁。”
“她没嫁人吧?”
“那我可不知道。”郑县长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地大笑起来。
“不知道?我给你说,我给你个任务怎么样,把这个姑娘给我介绍介绍,做我的老婆。”
郑县长觉得挺突兀,又觉得年轻的司令员惊人的爽快,便说:“那好,我去跟她说说,你等消息吧。”
郑县长找到张烽,如此这般一说,张烽当即顶了回去:“你看他好,你去么。”
郑县长哭笑不得:“我去干嘛?张烽,你听我说,人家……”
关于皮定均,张烽早有耳闻。在涉县城边上的河南店,一举消灭300鬼子,使他一夜之间成了人人传颂的英雄,她是敬重他的。但是,把他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她可从来没有想过。“我不愿意嫁给军人!”她一口回绝了。
郑晶华只好找皮定均交差:“皮司令,你给我的那个任务,嘿,我没完成。”
这件事被搁置起来了,但是皮定均并没有忘掉张烽。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1941年冬天,五分区来了一位女同志,她被分到宣传科任文教干事,教唱歌、教文化。人们很快得知,她是来自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
而她,第一次听分区司令员做报告,就被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大大地“震了一下”。皮定均做报告,根本不用讲稿,讲起话来,手也动,脚也动,满脸都是表情,洋洋万言讲下来,一口水不喝,一句废话没有,他那爆发式的激情很快就把大家融化了、陶醉了。
散会了,她打听起皮定均的情况。
“这个司令员,以前做过文工团工作吗?”
“没有。”

“是个知识分子吧?”
被问的同志笑了:“他一天书也没念过,长征途中从战友的背包上学认生字,会签名,能看简单的电报,许多东西都是别人念给他听。”
“啊,是这样。”她真不敢想象,这会是个没念过一天书的人。
皮定均当然不知道,他的一次寻常的报告会在姑娘心中种下一颗珍贵的种子。但是,他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这一天,两极的电终于碰撞出了一朵小小的火花。
冬季反“扫荡”结束,天气转暖,皮定均从磁县回到分区机关驻地,快走到驻地的溪边,他老远就看见她在洗衣服,一双手在大石板上揉搓,好听的《游击队之歌》隔着小溪飘过来。
皮定均不由得心中一动,他吩咐马夫和警卫员先回去,自己径自走向溪边。
“是你啊,我们的宣传干事、教育干事!”他远远地喊她。
她站起来,她注意到,皮定均的脸上挂着反扫荡的辛苦,比第一次听他做报告时要瘦些,但精神依旧,眼睛圆圆的,亮亮的。
皮定均坐在一块被水冲刷得溜光的大青石上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洗衣服,不怕狼吗?”
“哪有狼啊?不怕!”
“你是哪里人?”
“浙江省绍兴。”
“你们浙江出美人。”
“我的母亲是很漂亮。”
“你也很漂亮啊。”他笑起来。
她的脸微微红了。
“开个玩笑,姑娘们都喜欢人说漂亮。”他停顿了一下,“仗打完了,我最近可以休整一下,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在司令部。你明天可以到我那里去一趟吗?”
她点了点头。
“我想学文化,人家都说你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同志,我想请你做我的老师。”
皮定均什么都想学,学写字、学数学、学写诗、学音乐……多亏了她是个学文科的大学生,样样都来的。
他先学会了背《孔雀东南飞》,又学会了《木兰辞》,皮定均十分聪明,一点就透。学完了“唧唧复唧唧”他还嫌不够,又要她连词带谱地教《秋水伊人》。
后来她开始给他上数学课。他像是一个聪明的可爱的又顽皮的孩子。
皮定均也觉得,自己在这个姑娘面前,心情总是特别的好。难道说,这就是爱情?
当他们的课讲到公倍数、公约数时,他兴奋极了,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我今天懂了,学文化不光是上识字课。你多好啊!你好好给我讲,我有决心学文化,这就是文化!”
她的两只手被他抓在一起,她觉得他的手非常有力。她向外瞟了一眼,小院的门前有人进进出出,她不愿被人家看到他这样攥着她的手,可是,她没有把手抽回来。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脑子里装进一大堆概念,也装进了美好的憧憬。他骑上他的青骡子,上前线去了。

战争中有火有血,但也有诗有爱。
皮定均的马夫和警卫员都发现,每当司令员回一次司令部的驻地西达城,他的心情就特别好。
又一次紧张的战斗之后,他又见到了自己的“教员”。
新的一堂文化课开始后他就问:“刘师长要求,司令员要亲自动笔写军事报告,我怎么能学会这个?”
“你从写日记做起吧。”她回答说。
为了鼓励他写日记,第二天上课时,她送给他一个装潢和纸张都很精致的本子,那是她从北平带到根据地的。她已经用过一部分,记的是太行山民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