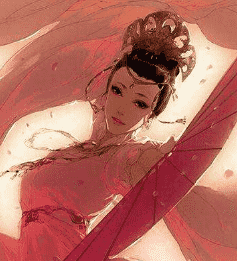图像和历史研究有什么样的关系?让图像不沉默
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些什么?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五岳真形图》。很明显这是一幅地图。按照日本小川琢治、英国李约瑟的解释,这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因为这个图上标了很多“从此上”,还标志着哪里有石头、哪里有药材、哪里有仙草,还有哪里到哪里是若干里。问题是,这个地图在道教里,变得越来越抽象化、神圣化、秘密化,变成了道教画的符。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地图到文字,从文字到道符,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可以捉摸思考的地方——如果只是地图,怎么会有神秘力量呢?只有抽象化、秘密化、神圣化,它才能够成为道教的有神魔力的东西,而且道士才能垄断它,否则的话谁都可以画。
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这个欧洲教堂里的塑像、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观世音像、福建德化窑何朝宗款的祥云观音,和日本长崎大埔堂曾经作为圣母的观音像。同样都是这个形象,她可以是圣母、是观音,而且她在欧洲、中国、日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曾经说,15世纪之后,中国的观音像传到欧洲,曾经影响了欧洲圣母像的制作;但是欧洲的圣母像通过传教士16世纪传到中国以后,又对中国绘制观音产生影响。看看吉美博物馆藏的观音像,她的胸口是十字架,还是璎珞?又比如,福建德化窑何朝宗款的祥云观音是很有名的,在明清之际曾经出口到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有过天主教迫害,日本禁绝天主教后,长崎那些顽强的天主教徒不能直接用圣母像来礼拜的时候,用的就是观音像。对于同一个观音形象在不同地区的流转和崇拜,我们能解释出什么内容来?其实这其中有很多可以思考的。

第三个例子是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洲16世纪画的人体骨骼图,被收录到欧洲一本人体解剖的医学书里,这个人体解剖书被传教士在明末翻译成中文,叫做《人身图说》,用了同样的骨骼图,但又加上了很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样传统中国的标识,在中国刻板印刷。可是有趣的是,这种人体解剖图,没有在清代的医学界流传,倒是进入画家笔下,清代扬州八怪罗聘的《鬼趣图》里,就用了这个骨骼图来画鬼。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挪用,把科学性的插图变成艺术性的绘画,把人体骨架画成死后的鬼形,掺入了很多阅读者和绘画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想象,这其中也可以解释出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图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中国艺术史领域,我们有很多东西还不能很好地解释,也许我们需要更多努力来探索图像背后的东西,逼迫图像开口说话。我觉得现在的图像解说往往停留在对内容描述说明的阶段,需要一些新的解释方法。我建议大家去看美国记者约翰·道尔的《拥抱失败》,这本书曾得过普利策奖。书里讲1945年后日本如何从战败中解脱出来,从容地接受失败。我们可以看他是如何利用日本的海报、漫画,包括像流行歌曲这样的一些资料。其实,解释恐怕是将来图像研究中最需要加强和改变的地方,当你能够在图像之外的历史文献中找到一些资料来印证、配合和解说图像时,图像才能不再沉默,才有可能从图像变成文献,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