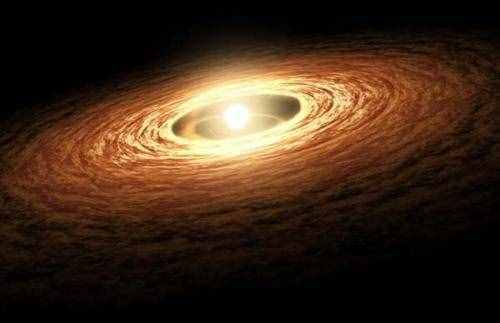“祭祀”唐代的农村布局,私人与公共区域是这样的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见史简谈史的《唐代的农村布局,私人与公共区域是这样的》,希望大家喜欢。

“村”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走入唐代的村庄里,除了一般的居住房舍外,较值得注意的便是提供祭祀功能的“社”。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一般村户数都不多,这样一来,“社”这样的一个空间,便成了相当明显的地域标志。而辅助标志的,往往便是村中的树。
在此所希望讨论的,是代表土地祭祀的“社”,而非一般民间的结社问题。
从先秦时代开始,社树便已经是标志地域的辅助工具。鲁哀公便曾向孔子的学生宰我请教“社”,宰我回答:“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因颇有曲解而受到孔子批评,然社树的采用,总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为主。据《农书》所载:
唐有枫林社,皆以树为主也。自朝廷至于郡县坛壝制度皆有定例,惟民有社以立神树,春秋祈报,莫不群祭于此。
因为唐代农村的神主,大多是设在神树上,而非一般想象的神坛上头。
说明至少在唐代,社已经成为了独立而鲜明的祭祀空间,当中社树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的民间结社中,也包括着祭祀土地神的“社祭”。相对于国家的“社祭”,其所代表的是国家本身,但是民间“社祭”指涉的则是该地区的土地神。社神是公共意识的投射,是村社的精神中心,同时社神祭祀的公共性活动,又为村社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维系力量。在此,“社”依旧只是个模糊的民间组织与祭祀行为,未若社树那样具有明确的标的性。
南北朝以来,村已经从里的架构中独立出来,成为一行政单位,在祭祀上也是如此,里社为村社取代,里之社树也成了村之社树。“社”与“社树”渐渐相依,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南史张敬儿传》里便有相关的描述,“梦居村中社树欻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白居易〈和古社〉诗里的叙述,更让我们清楚理解社与树之间的相依状态:
废村多年树,生在古社隈。为作妖狐窟,心空身未摧。妖狐变美女,社树成楼台。
树因社灵,多年祭祀下来社与树彷彿已经不可分割。聚落迁移之后,旧有遭到了废置,社树也走出该地农民的生活。废置前如社神一般让人感觉亲切,废弃之后又为一股阴森感取代,成了传说中狐媚妖物的居所。然而,这只是特殊情境下的产物,多数的“社”依旧保存着护庇村落的心理支柱,见元稹应白居易所作〈古社〉一诗:
绕坛旧田地,给授有等伦。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社公千万岁,永保村中民。
在元白二人的诗中,古社虽是描写村庄之事,却也充满了政治的隐喻。在此古社如同国家,妖狐则是佞臣,古社的落寞与妖狐的作祟交叠下,却营造出一股乱世升平的假象。纵使如此,元白二人依旧对于国家抱有相当的期望。
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王建的诗里,只是树种因地所宜有所改变而已:
我家家西老棠树,须晴即晴雨即雨。四时八节上杯盘,愿神莫离神处所。男不着丁女在舍,官事上下无言语。老身长健树婆娑,万岁千年作神主。
这也表示社与树间的关系未若一般想象的那么直接,有时也仅是单纯形貌颇值得赏玩,引来路人的祭拜而已,张籍便曾盛赞某树形貌之奇,“若当江浦上,行客祭为神”。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类型的树则不会引起太多的空间联想。像这样因为某种原因引起民众的主动祭拜,在历代史料中也不难找到,从秦汉时代流传至明清的“鲍君神型故事”,便说明了民间祭祀树的风俗。这样的树最多也只有路标上的意义,并不会引起什么村落空间的联想。
无论如何,社与树在村中标志了一个不可取代的空间。除了提供较宽广的空间予村民聚会,更成为举办各种祭祀活动的最佳场所。尤其是春社与秋社,更是热闹非凡,从“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开始,家家户户都放下手旁的工作,前往村里的社树一旁;“酒熟送迎便,村村庆有年。”人人尽出私藏,好好的狂欢一番;到最后“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纵使酒终人散气氛仍是祥和,无丝毫的苍凉寂寞。
这些社树,可说是乡村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标的物,在村落的祭祀中甚至称之为“神树”,是国家礼制下所认可的祭祀空间。更甚之,他们成为一种印记性质的集体记忆,广泛的存在于群体之间,深烙于群众的潜意识当中。明清时代流行的“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谚,其所指涉很有可能便是其原居地的社树。纵使离开了家园,这些农民世代间依旧流传着这样的共同意象。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乡土的农民,抱着对于家乡的思念,一代一代的传述转变成大槐树的集体记忆。在上述元白诗中的农民较为幸运,却也深刻表现出他们安土地着的个人期待。
至于农村中农民的住宅空间,其实难有一个定论的空间。农民住家面积、用料乃至于内部的摆设,往往取决于各个家庭的资产多寡。又加上唐代相关的史料实在少见,要确切的做一番描述有相当的难度,却也不能够因此就避开不讨论。因此,依旧有必要利用现有的资料,稍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唐代不仅以均田制保障农民的耕种土地数额,居住房舍也是如此,此见于《唐六典·尚书户部》:
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
唐代的一亩土地,依大亩作计算,相当于362.45平方米,纵使扣除古代地广人稀的因素,这样的居住面积还是可能显得过大,若以平均五口的方式计算,则每个人可以分配到到超过66平方米左右的居住空间;若以小亩作计算,一人可分得30平方米以上的生活空间,虽然稍微狭窄了点,但也比较符合一般的想象。
规定上虽然说三口以上每三口加一亩居住地,实际上超过六口的家庭却不多。整理唐代西州户籍,四十五笔资料中超过六口的家庭也只有四户,在比例上连一成都不到。相对之下,三口或不足三口的家庭高达二十八户,比例上升至六成以上。换句话说,许多农民家庭的生活空间可能比想象的更大。若是上述的法规皆得落实,在此可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至少在西州地区,唐代的农民享有颇为宽敞的居住空间,与往常想象中的贫困、拥挤的空间或许有着相当的差距。在两税法时代以后,家族的规模略微扩大,家庭享有的生活空间,也可能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
在房舍的外型方面,因为南北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大致上北方多瓦房,南方多茅舍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瓦房在中国北方已是长期存在的房屋形式,当中四合院又常见于史料的记载。王梵志的〈生坐四合院〉、〈好住四合院〉诗里,清楚说明了诗人居家空间分布的格局。唐代住房分布与面积,依旧是四合院的格局,或许说明了四合院在当时北方式相当常见的住房结构,其概略的面积分配如下:
敦煌文书所载唐代住房分布与面积
除了四合院或三合院特有的中央院落外,较值得注意的便是“堂”的面积,显示了祭祀的空间在一般的农家中,依旧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唐代南方依旧是待开发的区块,住屋的形式也较为简陋,往往以茅舍为主。今日所遗存的资料中,有关南方田舍的纪录仅见于文字的描写,缺乏更为详尽的资料,具体的描写可见于陆龟蒙《田社赋》:“江上有田,田中有庐。屋以蒲蒋,扉以籧篨;笆篱楗微,方窦疏棂。”蒲、蒋二者皆为植物名;籧篨意味破烂的草席;楗微者,意指可关闭的木门。可见陆龟蒙的田舍是以茅草为屋,草席作门,由此可以发现到,江南地区的茅舍无论在造型与结构上都相当的简陋,无怪乎王祯读此亦感慨“状其简陋,非久经其处,不能曲尽若此。”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南方农村的落后。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绘有田舍的想象图,虽然时代有别,在形式上却与陆龟蒙田舍的描述颇有雷同,故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外在结构的封闭与开放
纵向整合顺畅,横向却颇为滞塞的流通模式——巨区理论。
藉由各层级都市的向下资源统整,各地方的物产皆得以顺利的运输至中心都会。相对之下,横向的流通却往往只能经由标准市镇整合后达成。由于糊口经济的维生方式,多数农民的需求经由标准市镇即可满足,某种程度上阻塞了上下间的流通。
巨区理论纯然为一自然经济底下的架构,与实际农村的情况多少会有偏差。传统中国的都市多以政治与宗教为核心,也展现出一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唐代的地方制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纵向整合,只是在细部上有着相当的差异。如此垂直统合的方式,这是地方基层制度上的一个共通特色,并非中国地方制度上的特色。
笔者的描述,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农村的开放与封闭与否,只是表示了体制下存在着这样的空间。空间的封闭与开放,其实取决于人为有意的经营。在人为的经营底下,一个看似封闭的空间可能极具开放性,相对的开放的空间亦然。这种难以言喻的感受,只能真正的走入其中,方能略略领会一二。
参考文献:
《四书章句集注》《农书》《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南史》《白居易集笺校》《元稹集》《全唐诗》《风俗通义》《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唐会要》《历史研究》《唐六典》《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王梵志诗校注》《中国家庭史·隋唐五代时期》《甫里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