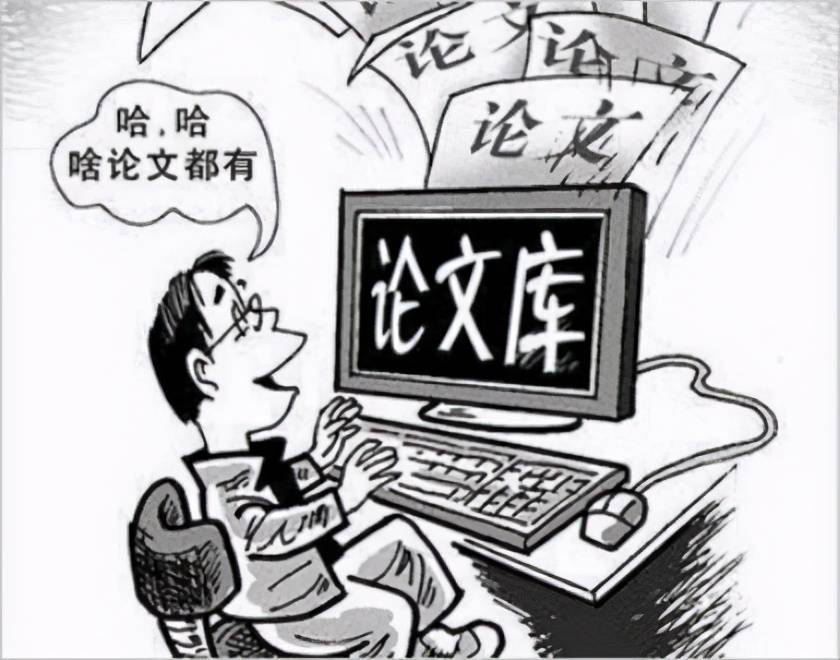汝怎么读(汝是lu还是ru)

电影《路边野餐》剧照
1.
火车开,下南方,白桦一株一株往后退,骑楼一栋一栋向前来。高铁穿过大半个中国,余下讲粤语的乘客。如此睡过一个天黑,下了床,坐窗边,好一阵才缓过来。
故乡的名字叫湛江,在中国地图的小角落,与海南岛隔着一道浅浅的海湾。湛江地处雷州半岛,据说是因为经常打雷,有此名称。雷州古代是南蛮之地,海盗、流寇、游侠盛行,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雷州则是素产彪悍之人,古时候官员都不敢去那,怕有去无回。
很多人听过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珠海,但没听过湛江,即便听过,脑海中飘过的也是湖光岩、白切鸡、黑社会、海南岛,加上湛江多次因走私、贩毒、台风等事情登上新闻,导致外省人以为这是一片滋长罪恶之地。
其实,湛江曾多次出现在领导人的南巡讲话中。比如1960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湛江,说:“北有青岛,南有湛江。”但六十年过去了,青岛的发展早已把湛江甩在身后。湛江本可能在改革开放后和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崛起,可惜被一群贪官污吏耽误了,九十年代的湛江官场乌烟瘴气,地方治安一团糟,大投资商根本不敢来,进入千禧年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湛江的方言混杂,广州白、湛江白、雷州话、客家话、普通话、电白等语言遍布在五县四区,五县(市)是徐闻县、遂溪县、廉江市、吴川市、雷州市,四区是赤坎、霞山、坡头和麻章,不同区县操的方言不一样,比如霞山和赤坎讲湛江白和普通话的居多,但雷州完全是雷州话的天下。
本地主要有三大语系:一种是湛江市区白话,偏广州白;一种是湛江本地白话,偏雷州话;还有一种是廉江话,又称客家语系的“涯话”。在外省人眼里,广州话、湛江话、廉价话、雷州话、吴川话等等,好像都差不多,但在本地,这些被分得很清,你要是说雷州话是白话,别人会白你一眼。
譬如讲:广州人表示“不知”,他们会讲“唔知”,“唔”(m)有否定意。但操持湛江白的人更惯用“冇”(mu)。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广州的口头惯用语“唔该”,在湛江也是这个讲法。
雷州话和广州白差距更大。雷州话以雷城话为主,从属闽南语,雷州人称呼“你”,会讲“汝”(ru),而广州人讲的“你”近似于“nei”这个音。
我爷爷辈是雷州佬,在湖光镇有一个蔡屋村,就是我爷爷住的地方。到我父亲这代,他们赶上城市化大潮,就在赤坎区买房,城市乡村两地跑,所以我自小生在市区,对乡村的认同感很低,身上也不见雷州人的感觉。我母亲还能辨别野菜的不同种类,到我这就都是去超市、商场或小卖部买东西了。
我不太会说雷州话,又很少回农村,母亲怕我忘本,就隔三差五催促我回去走亲戚。我小时候不懂规矩,见亲戚都木木的,有时会弄得气氛很僵,后来见多了亲戚,基本就知道他们问什么,有一次亲戚来我家,夫妇,男的四十岁左右,脑门透亮,浓眉大眼,身段像粽子,他爱人卷发浓妆,穿一身黑,说话像机关枪。他们一进门就给我母亲塞红包,然后热情跟我说“又高了”、“又瘦了”之类的话,知道我就读于文学院,就说:“文学,文学好啊,以后出来教书或者做公务员,很有前途!”
湛江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本地真的有一条江叫湛江。其实,湛江以前叫“广州湾”,这个名字从清朝延续到法国殖民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想在广州湾筹建一个市,时任吴川县县长李月恒受命担任广州湾市政筹备处主任,负责起名工作。他知道本地曾得名“椹川县”,就依样画葫芦,让广州湾易名为“椹川市”。又过些日子,政府感觉湛江靠海,以海为天,市名应该体现出水的特色,就把木字旁改成三点水,也就是今天看到的“湛江”。

2.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老城区,告诉我哪些地方过去是一片汪洋,哪些地方历史比较悠久。改革开放后,市政府利用填海造陆等办法扩充了湛江市区。现在,如果你去到赤坎或霞山的中心城区,成片成片的摩天高楼,兴建起来的购物中心,五颜六色的LED屏幕,酒吧、电影院和后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群。但也许相隔不远,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观,小平房,烂尾楼,棕榈树,还有许多按摩店,看起来非常老旧。
外地人来湛江喜欢去湖光岩,那是一个以玛珥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的生态公园,在全国有些名气,但本地孩子去腻了那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每次郊游,想不到去哪里好,就会去湖光岩,同学就抱怨:“又去湖光岩,都去几次了?换一个啦!”
湛江不缺碧水蓝天,所以对于湖光岩这种景区,市民不会大惊小怪。如果有人想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去去湛江,每每晨光初照、云翳满天,游客沿着市区内两岸的白石雕花护栏一路行走,美人蕉、酒瓶椰、黄金榕、棕榈、紫薇、剑兰等亚热带植物尽收眼底,如果去金沙湾,还能捉一捉螃蟹,看斜阳浸染在海平面。在湛江,蓝色和绿色是最普遍的,所以,作家冰心去湛江游玩时曾说:“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
这座城市总是伴随着湿热的雨,春夏秋冬,说不清什么时候,雨就倾盆而至。有时从早上下到晚上,有时十几分钟后,雨就停了。撑伞前行,趟过一片水洼,临街的小贩正沿街叫卖,绿豆冰沙,龟苓膏,肠粉,芝麻糊。足球场,光着膀子皮肤黝黑的男孩在桥下躲雨,他们上半身两个黑色如伤口一般的疙瘩格外显眼。在我的母校,一座桥连通学校的足球场和教学楼区,每天放学,都有孩子走下来踢球。
在湛江,抬头仰望,一条淡蓝的绵长大河就悬在头顶。它无边无际,追溯不到源头,只是模糊消失在海港的另一边,那是海神的透明袖袋,雾气缭绕、缀有彩云。栖息在这条河里的不是鱼儿,而是形状不一但柔软洁白的云朵,悠哉长鸣的海鸟。清澈的大河,令它们无处遁身,顺着河的流动,云朵们有条不紊地游移。天近暮色,夕阳沉水,一股红流便在河里漫开,缀染了河里的生灵。人们看到云儿羞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摇曳身姿,伴以暖风轻吟的律曲,直到夜幕落下,曲终云散。这时候,城市的人们大抵是疲倦的,所以墨色的大河浮起了数不尽的星辰。
到了雨季,天上的大河河水便要溢出来了。一粒粒饱满的雨滴,温柔滴飘下,落在东海岛银白的长滩、湖光岩蕴秀的山角、老街巷古色的骑楼、法式建筑掉色的墙壁、接天长廊荡起的清浪,还有,一把把撑起的雨伞和一张张黢黑的沧桑面庞上。清新的雨香,渗入蓝色小城的每一寸土地。
湛江水分多,大雨能持续许多天,赶上台风天,便真是“路上行人欲断魂”。有人做过统计,建国以来广东省内登陆的最强台风里,湛江在前六席里占了四个,其中,湛江人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的“萨莉”,256人死亡,23000人受伤,全市停电、停水、停工、停课,供水和交通陷入瘫痪,那一年台风登陆时,我的父母就守在昏暗的屋子里,连续数日无法出门。有了“萨莉”的历史,后来的“彩虹”、“山竹”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湛江靠海而建,本地人从小和水打交道,盛产“浪里白条”。我父亲就曾住在渔船上,随船主人出海打渔,摇摇晃晃的船板,空气中满是潮湿水汽和鱼腥味儿,被捕上来的鱼在网内拍打到没有力气。父亲回到陆地后偶尔提起水上的日子,得空时他会去海边走一走,他喜欢在海边玩“水上漂”,简单来说就是从海滩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块,投向海面,看看它能够弹起几次。父亲是玩这个的高手,他一次能让石块在水面弹五六下,引得小孩子驻足旁观。
和父亲相比,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从小下地种庄稼,在芭蕉林里捉迷藏,长大了些,就继续在农村里当老师。那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六块钱,农村里教师紧缺,六个班级由七个老师管,一位教师能兼任语文和数学老师,而我母亲授课的同时还要管财务。
农村里的教室是平房,夜晚要点煤油灯,有一次母亲批改作业、眼困了,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打下来,差点着火。在八十年代的湛江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气,吃水要去井里打。在这样的条件下,民办小学的教师每个星期还要抽出两晚无偿给农村的文盲青年上课。我母亲就这样做了十几年教师,直到八十年代末,大批农村人被允许进城,她才加入了进城大军。
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就在城里,农村成为一个逢年过节回去的地儿。我小时候和爸妈住在百园路一栋普通公寓的二楼,在外可以看到铁窗和制冷器的那种楼。不远处就是新开发的碧桂园楼盘,那处楼盘几年前还是一些老旧房屋和一个小学校,学校据说闹过人命,风水不好,但现在,它已经是一片挨着商业广场的黄金地段,和新楼盘相比,我家在的小区就显得寒酸。
小区是一座小城市的缩影,理发店、按摩店、早餐铺、茶庄、停车场,家家户户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是我母亲一下楼就和别人打招呼,唠几分钟家常,说说别人家孩子的好,社区边的街巷,基本是一个熟人圈,有时候母亲去买点东西,比如一箱牛奶、一袋水果,忘带现金,打个招呼就能拿走,因为店主信任你,知道你下次会一起付。
我童年就在这个小区度过,初中做过一段时间寄宿生,但不习惯,后来改成了走读,每次回到小区,我都要买一碗豆腐花。豆腐花在我家门前的十字路口旁大排档,那里卖肠粉、艇仔粥、烧蚝、绿豆糖水、芝麻糊,也卖豆腐花。
中学期间,每天夜晚十点,我从学校归来,经过大排档,缭绕烟雾的飘香就会让我放缓脚步。但伸手摸了摸裤袋,脸色犯了难,还是回家了罢。心道闲钱不多,下次再光顾。回到家,豆腐花已经在棕红色的木桌上。还有烧烤、绿豆糖水。
在广东,豆腐花是很常见的小吃,便宜且好吃。做一份豆腐花,须先将黄豆浸泡,待黄豆吸饱水分,打浆、滤渣、煮滚,降温后“冲豆花”,不同分类的豆腐花用材和步骤也有区别,据说,有用豌豆、蚕豆代替黄豆的,在香港,豆腐花能配芝麻糊,讨巧者令其呈现的外观如同“太极”,故而人称“太极豆腐花”。
但我吃的,不过是最平凡的那一类。巴掌大的碗,白花花,滑溜溜,灯光洒下来,它便闪闪发光。用勺子轻轻截下一块,刚入口,它便化开了,留下甜意于舌尖。在故乡吃的豆腐花,是安定的甜,以至于我心觉天底下的豆腐花都如此,不甜不是豆腐花。报考天津的大学,一路向北,才知道甜党咸党的纷争。
我在天津尝过的其实叫豆腐脑。起初,我以为它便是北方人眼中的豆腐花,不过是甜咸有别。后来经有人提醒,才知道二者成分虽无大区别,皆为豆腐的中间产物,但豆腐脑较嫩软,而豆腐花更凝滑。可古人好像不分那么清,清代人写的《随息居饮食谱》如是说:“豆腐,以青、黄大豆,清泉细磨,生榨取浆,入锅点成后,软而活者胜。点成不压则尤软,为腐花,亦曰腐脑。”
在天津,豆腐脑一般与老豆腐作区分,“豆腐脑浇卤,老豆腐则佐酱油等素食之。”“要想胖,去开豆腐房,一天到晚热豆腐脑儿填肚肠。”豆腐脑似乎是天津颇有名气的吃食,清晨拨开雾气到食堂,桌上常见的早点,煎饼果子、豆浆油条,还有就是豆腐脑。
但我更喜的还是豆腐花,在广东生活了十七个年头,我已经被南粤故乡的口味惯坏了。如今回想起故乡,眼前出现的,除了一练澄澈的蓝天、躲在石缝中的青绿色螃蟹、过道狭长人影疏疏的老街,还有便是那处十字路口旁的大排档。墙壁定然是灰灰黄黄的,服务员们来回走动,操着家乡话,大意是:“不要催,不要催,很快就好。”马路旁人们围坐一块,场景闹哄哄,有的人擦肩而过,没想到就是隔着一条马路的熟人。待到大清早,大排档休憩,另一个路口,卖豆浆的小店开始冒热气,早晨的湛江,是豆浆、肠粉、湖光奶和牛腩粉的天下。

3.
初中在一所叫培才的私立学校念书,从家到学校要二十几分钟,摩托佬不怕死的话,十分钟就到。在湛江,马路上摩托佬一个接一个,皮具店传来《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笑声。校内收拾东西的同学仔,津津乐道《廉江二摩强》,这是本地一个热门节目,有同名歌,不但摩托佬中意,我们班男生也爱听。
那时我们喜欢谈论漂亮姑娘,尤其是热情奔放的,在广东,她们一般被调侃为“姣婆”。姣婆原意是讲比较懂发骚的女人,有句话叫“又怕生仔又发姣”。一般女仔不中意别人说她“发姣”,但如果是亲密的人,开开玩笑,倒也无伤大雅,毕竟大家都很喜欢起外号,四眼、鸡肠、肥佬、炮王、姣佬、菜头什么的,其中跟吃有关的外号不少。
初中是一段相对无忧无虑的生活,血气方刚的本地生还有闲心打架、沟女,我初中时比较沉寂,那时自己矮个子,头发长,有点像《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仔(但没染发),在我们那,管我叫“女态”,就是生得似女仔。我那时没读什么研究性别观念的书,只知道周遭男生,看不起长得像女生的男生,而我的观念,也随他们,所以当某一天,一个女生说我“似女仔,不似个爷们”时,我假装看窗外,内心却耿耿于怀。
中考后,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都开始为高考发愁。我的高中叫湛江一中,这里的同学大致可分为“本就在上面的”和“从下面上来的”。“本就在上面的”是指初中就在市区的学生,“从下面上来的”泛指从偏远地区考入市重点高中的学生。在偏远县区,很多家长不奢望孩子考进重点大学,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我高中有一位同桌就是从下面上来的,他告诉我他的初中生活,教学设施老旧,社会治安混乱,曾有学生走在路上,被蛊惑仔围打。到了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大量飞虫大闹学堂,去食堂吃饭,还可能遇到小团体打架。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无心向学,中考后就成为社会青年。学校会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一两个班里,这些人是学校的指望。
我经常从他那里打听故事,虽然都是湛江人,我们的生活却截然不同。市区里的湛江安稳舒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三线小城模样,海阔天清,气候宜人,适合慢生活。但市区外的湛江就凶险许多,网络上流传的湛江黑帮轶事,多数在偏远县区,走私贩毒,深夜火拼,贾樟柯在《江湖儿女》里描绘的黑社会景象,就让我想起了老家的古惑仔。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粤西的黑恶势力横行霸道,外省人来这里都要小心翼翼。
从初中到高中,我喜欢上两件事。一件是踢球,一件事写作。中学的时候,刮风下雨天,我也会去球场练球,有时候没有球,就踢塑料瓶,用鞋子或包包摆两个小门,把塑料瓶踢进门,就算得分。
高中文理分班,文科班组不起球队,爱踢球的人就以外援的形式,加入认识的理科班球队里。我参加了两个赛季足球联赛,前一次帮助球队拿了亚军,后一次收获冠军。我加入的第一支球队名叫“城管”,到了第二个赛季,我们的球队曾取名“刚果”,和一个非洲国家重名。
高中联赛能办起来,多亏了一些天时地利人和。那阵子,校领导正响应上面号召,大搞校园足球,学校里一些爱踢球的同学,就和老师提了举办校园联赛的主意,一拍即合,但真的办起来,光是协调各支球队时间、场地、找裁判就颇费周章,做这种事吃力不讨好,犹如球场上的裁判,执法森严,两头得罪,执法宽松,别人又说你没水平。
联赛办起来后,发起人成为第一届一中足球协会主席。他每次来球场都提着个公文包,派头仿佛办公人员。他跟各支球队的“大佬”都很熟,维持关系是把好手,他当主席,看起来平平庸庸的,但大家都服他。
一中的足球联赛很简陋,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临时找裁判、没有灯光导致天黑后场地内一片黑暗,以及赛程和其它学校活动的冲突等,但它为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大学放假时返回母校,足球场仍是我和朋友重逢的地方,踏上绿茵场,回望三年放学后踢球的时光,那时候,我们15届的最开始是学弟,初来乍到,免不了被老油条们“霸场”(占领场地),后来,老油条们毕业了,我们成了学长,又结识了不少热爱踢球的“高一仔”。这块球场热闹的时候,每一个小门前都有人比赛,如今,我们放假才来,绿茵场就颇为冷清了。那些老油条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远在他乡,还有的,偶尔还能在一中的绿茵场,或者湛江其它体育场碰面。猪哥是其中的老熟人,我们每一次踢球似乎都能见到他,据说他收集有一中各届知名球友的联系方式,我们笑称他是湛江足协荣誉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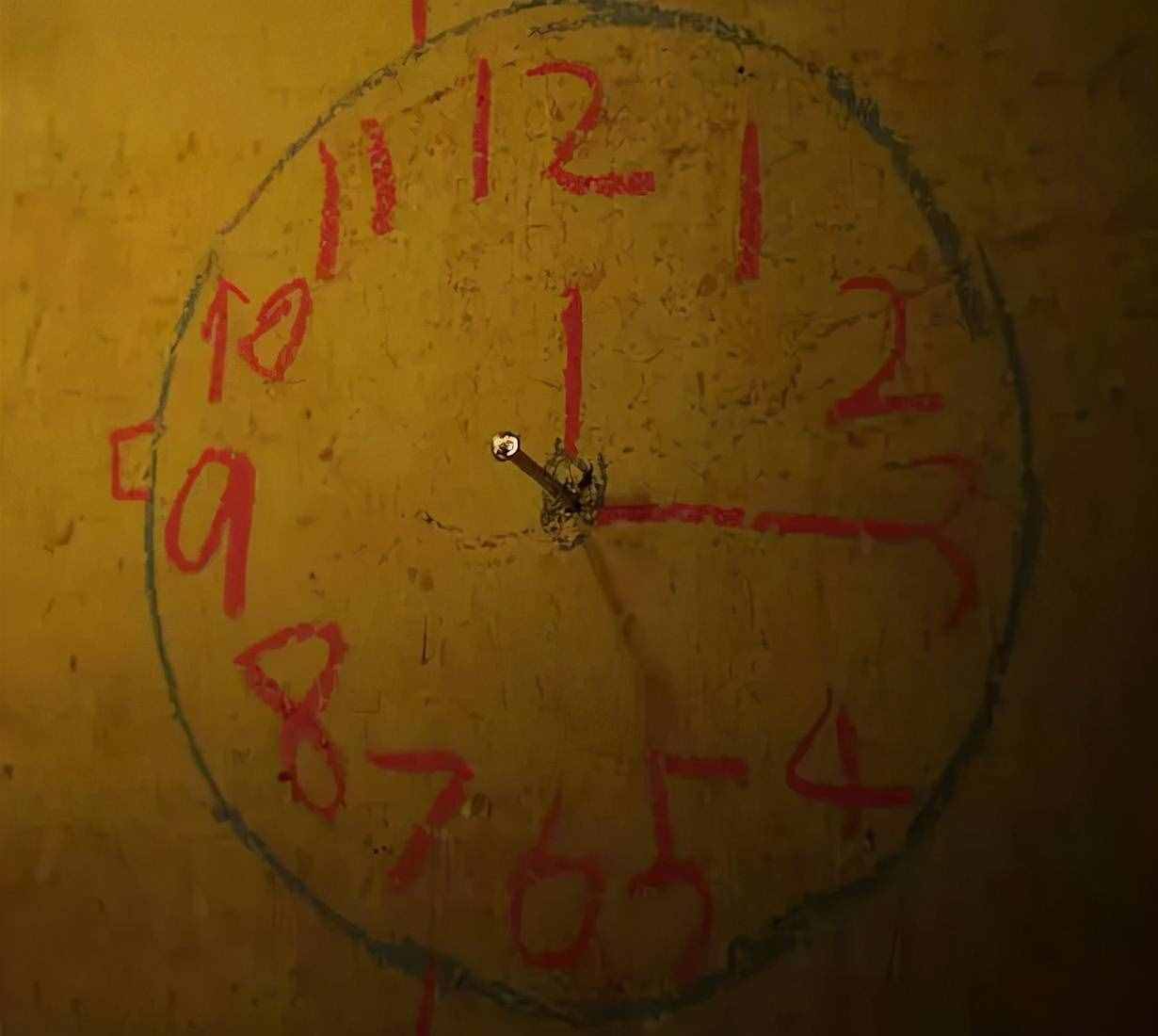
4.
高中毕业以后,一起踢球的机会少了,能不能集齐人都是问题。我的踢球习惯渐渐荒废,写作倒是频繁起来,大学后,我业余靠写作挣钱,文章发出后,编辑会要我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地址和邮编。有一次,我在回复里把这些信息一一敲入,写到邮编时,我却重写了。
我第一次输入的数字是524000,那其实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邮政编码。我在湛江一中读书的时候,经常要写这个数字。
高二时,我心血来潮写小说,妄想通过比赛一举成名,某日放学后,我就屁颠屁颠把稿子塞进信封,按要求填好地址邮编,郑重地走到校门外的墨绿色邮筒,石沉大海。
投稿没有回音,我只好继续收心学习。作为一名偏远城市的普通学生,我的高中生活并不像青春电影渲染的那么叛逆、激烈,多数时间,无非是学习、踢球、读书,和同学聊八卦,放学了去报刊亭看会杂志。高中常看的杂志是《读书》《看天下》《足球周刊》,还有《萌芽》《作文素材》《故事会》之类的,那会儿杂志间也有鄙视链,比如看《读书》的看不起看《萌芽》的,看《萌芽》的看不起看《故事会》的,大家考试都抄作文素材。班里女生爱看《萌芽》,有些男同学酸,私下说郭敬明、韩寒有啥了不起的,如果小说发在了《萌芽》,就要改口谢谢编辑知遇之恩了。
我那时常借同学的杂志看,还有《明朝那些事儿》这一类书,口头说是积累写作例子,最后真派上用场的还是伟大作家布什沃索德。高中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文言文作文,啥话题都套入文言文里,通用模式是主人公(“我”)通过某种渠道(做梦或穿越)和古人对话,最终恍然大悟,价值升华。以至于老师收到我的作文,调侃道,不用看,又是文言文。奈何我功力浅薄,当时的文体其实是文白混杂,新鲜度一过,分数就打了折扣。我的语文老师坐不住了,她建议我放弃文言文作文。其一,现场限时写作文言文风险大;其二,作文原则上应当推广白话文书写。
我没有跟老师抬杠,从了她的意见。那阵子,班里流行作文素材,报刊亭里就有成堆成堆卖;那阵子,议论文是主流,全班很少人敢涉猎记叙文;那阵子,排比句长盛不衰,憋不出话来,就套上几个事例,大段大段排比。
我进入了议论文的海洋,但我比较有原则,素材不想拾人牙慧,加之我正为数学英语发愁,无暇记忆“高逼格”人名,于是我成了班上虚构名人名言第一人。
我不清楚是谁开了这个先河,但论虚构的名头,我掏着心窝子说,班里没人比我响亮。动起念头,我便说造就造。投身议论文的第一次月考,我生造了拿破仑崇敬之人“让·雅克·方济各”神父,借他之口说出我编造的话。开篇又借某俄国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弗拉基米尔·布斯沃索德”之口,直抒胸臆。改卷老师没空校对人名,看我说得有那么点道理,给了个不错的分数。为此,语文老师在课上点评了我的试卷,对我勇于在虚构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给予肯定,但号召我的同学切勿模仿。
高二以后,大家对成绩愈发重视,随着考试频率增加,排名、进步的表单都贴在教室里,不容我们回避。那时候会和几个同学比较成绩,有暗暗较劲的,有明着来的。有一位男同学,他考完试后常跟我说:“城哥,我不行了,这次考得好差。”结果对完答案,他又会贼笑,第二天老师就会说:“XXX同学,这次进步很大。”
还有一些成绩一直很好的,或者在单科信手拈来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题,她一下就明白了。天资平平但勤奋好学的同学,就会私下请教他们。
当时,班上还会在墙壁上贴一些激励学习的话,比如什么“今天的汗水明天的泪水选一个”“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正前方是高考倒计时,数字一天比一天少。
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事情也许算是“苦中作乐”,那些和同学互相激励的话语,偶尔的一些小幻想,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太压抑。设使高考成功,我如愿考上理想大学甚至往日发挥可以达到的学校,我可能会将这些辛苦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用高考的成功消解一切苦涩,但可惜我并未做到,尽管对了答案后我信誓旦旦,可高考成绩冷冰冰的数字不容我申辩,再多理由也无济于事。当然不只我一个人如此,一些在我眼里考试十拿九稳的同学,高考也失手了。一些日日夜夜奋斗的同学,只考到了三本学校。
高考的得失,是高中三年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是全部。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因为高考就回避那三年的记忆,这种“唯结果论”就无法让我真正坦然面对自己、面对我经历过的时时刻刻。人是记忆的产物,而记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所谓结果,记忆是没有结果的,你眼中的结果,只是一张网里的某个小点。当我谈起我的母校湛江一中,我谈起的是一段属于平凡个体的记忆,而不是一个励志或失败故事。
毕业后,离开学校会发现,和从前的老同学聚一聚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可能是实习,可能是兼职,还有人家离得远,假期时间本就有限,要找一个大家都舒服的时间并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再碰到校友或者一起踢球的同学,我就觉得很亲切,彼此熟识,相逢一笑,即便不说话也自然。
我喜欢张怡微写的一个句子:“密密麻麻的高三脸,眼睛炯炯有神,青春猝不及防糊了她一脸。”就是那种青涩而猝不及防的感觉,它在青春期时浓烈旺盛,但当你进入大学,当青春期一点点褪去,这种感觉也将一步步消失。
中学那时候,我们还未习得精致的妆容,我们在社交辞令上漏洞百出,我们有时拌嘴,我们有时热烈,我们还无法准确表达和理解许多词汇与感觉,我们一度以为一段关系将天长地久,中途却因为鸡毛蒜皮打起冷战等对方道歉。我们为了一个目标坚定奋斗、互相勉励,也在电话和里分享各自的悲伤与喜悦。
那些在下午六点的校园恣意奔跑的身影,如同夏花,转瞬即逝,却已经在记忆里生了根。以至于当我北上,在异乡的餐馆里听到陌生人讲粤语,那些青春的背影又会在我眼前出现,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TVB剧,无人维护的法租界建筑和一排排茶餐厅、烧烤店,也想起了那里的树木、空气、泥土、河流。故乡种种,成为流淌在我体内的另一种血液,像是阿多尼斯所说的另一种光明,是在我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和外部的黑暗时,把我照亮的光明。
于是我走在返回高中的小路上,那天雨刚刚停息,路边有流水,躲在蜿蜒曲折的石壁小缝,浸湿柔软的蜗牛与蚯蚓。我看了看足球场,又抬头望向教学楼的高处,此时此刻,大概仍有学生在教室静默冥想,亦或奋笔疾书?我坐在长凳上,看看天,看看云,看看曾经走过的路、待下课铃响,看见密密麻麻的青春脸从我身边走过。
我记得那天,朋友叫我去赤坎体育场,踢五人制的小场。我的茵宝球鞋忘在了北京合租房,只好再穿上高中用的球鞋,去到体育场。到体育场时,我见到了一位昔日踢球的朋友,他还是没变,可是,我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却沉默了好久。当我下意识地用普通话交流,而他仍习惯地用粤语和我不认识的人聊起近况时,虽然我们离得很近,却距离很远,那无法跨越的距离,就是我和过去的距离,看得见,摸不着,失落在记忆的青色角落。王小妮写过一首诗:“所有的人都在,只有你要的不在。”那天,我躺在草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天空看了许久。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我们的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