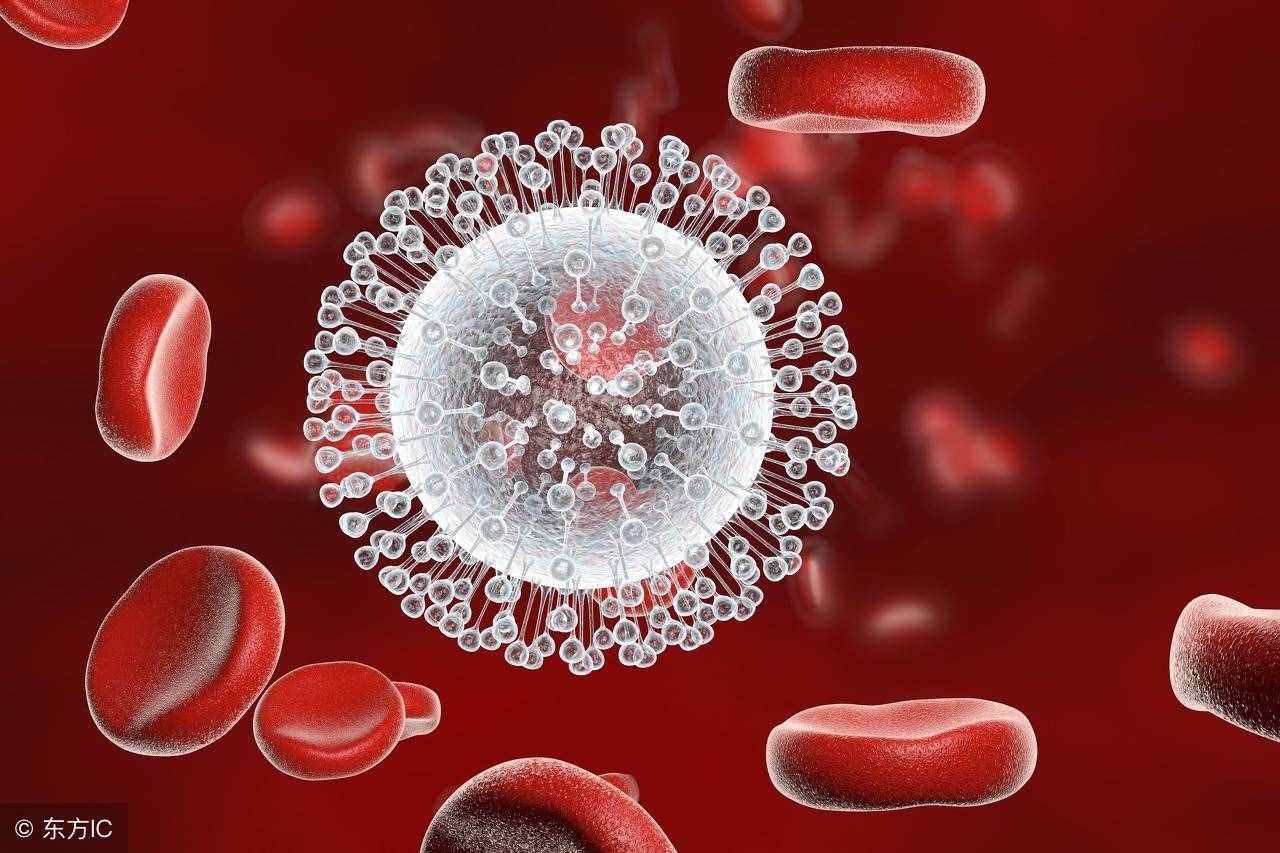永乐大典内容(存世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内容(存世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曲折回归路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21总第1000期《中国新闻周刊》

(6月8日,读者在国家图书馆“全景展厅”观看《永乐大典》。图/IC)
9册近年首次亮相的《永乐大典》,6月起在国家图书馆展出。这些《永乐大典》饱经风霜,有些在清朝时被翰林院官员从宫中盗走,后来流入古董市场;有些历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掠夺,被侵略者劫掠到外国,流浪数十年后才回归中国。每一本《永乐大典》都是孤本,价值连城。
清末以后,《永乐大典》就像一个沉入地底的史前遗址,世界上还存在多少本、流散在何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时不时就有新的零册被“考古发掘”出来,出现在图书馆、拍卖行、收藏家手中,乃至农民的家里。
目前全球已知《永乐大典》共有400多册及部分零册存世,与全本11095册相比,现存不到4%。这些零册收藏在8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241册、日本60册、美国53册、英国51册、德国5册、越南4册、爱尔兰3册。
《永乐大典》汇集了明初存世的七八千册书籍,对学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古籍宝藏,研究价值无与伦比。仅仅在现存的4%里,已经打捞出大量古籍的“孤本”,至少600多种已经失传的书重新被认识。
为了发挥大典的研究价值,曾经的皇帝私藏,以收集整理、影印出版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历时近一个世纪。目前国图正在研发《永乐大典》数据库,让大典上线。
回归之路
2020年7月7日,两册《永乐大典》在巴黎一家拍卖行现身,拍出640万欧元净价,买主是一位中国藏家。这是全球范围内时隔6年再次发现《永乐大典》零册。
《永乐大典》前一次现身是在2014年,在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长陈肃知道后,把照片发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请她帮忙确认。初步判断是原件,恰好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专程赶去汉庭顿图书馆,目验了这本大典。

(2014年,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馆藏图书中发现的《永乐大典》。图/中新)
“封面改装过了,但用的也是黄色硬皮,外观接近,内容都是对的。各种特征与真本一模一样,我看了非常激动。”刘波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册大典是一位旅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于1968年捐赠的,但馆内无人认识中文,一直尘封在仓库里,直到聘请华人馆员杨立维后,才发现了这册大典。
陈红彦说,《永乐大典》的鉴定并不太难,因为每一本都是唯一的,有卷目编号,检索目录就可以知道。大典的装帧也有严格标准,使用特制的纸张,这些特征都比较容易判断。这几年曾有人拿着“大典”希望捐赠给国图,开本大小都不对,一看就知道不是原件。
2007年1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专家组赴各地督导并核查古籍善本,陈红彦当时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那年在上海核查时,遇到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将手中藏的一册大典带回了国内。国图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了4次鉴定,认定是真本。
“每发现一册都是激动人心的事,像是天意,刚启动古籍普查就有了这么大的惊喜。”陈红彦回忆。此册为“模”字韵“湖”字册,一册三卷(卷 2272~2274),与国图原藏的两本“湖”字册(卷2270~2271、卷2275~2276)恰好前后相连。这一册2013年10月正式入藏国图,是目前入藏国图最晚的一册。
1983年发现的一册颇具戏剧性。当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基在县文化馆墙上的挂历里看到《永乐大典》书影,发现与堂弟孙洪林家的古书很像,便写信向北京图书馆汇报。这一册“天头地脚”(书页上下空白部分)已被裁去,用来夹鞋样。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文字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之后被国图收藏并修复。
曾持续调查、整理《永乐大典》20多年的古籍专家张忱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典的出现“可遇不可求”。
1974年,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张忱石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整理近些年新发现的《永乐大典》零册,并影印出版。60年代,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等人曾将当时存世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之后又有新的零册现世。
那时中外交往很少,要与国外收藏机构和个人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想看到和影印国外收藏的大典,困难重重。
有一年,张忱石听说日本有一册出现,具体信息一无所知,托多位访日的朋友查询,也没有结果。几年后,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去日本访问,执着的张忱石又请他帮忙打听。这卷大典刚好影印出版,章培恒订购一本带了回来,时隔多年,张忱石终于见到这册大典。
1986年,张忱石多方搜集整理的新零册影印出版,他花了12年,为影印版大典增加了67卷。
命途多舛
《永乐大典》编纂至今已过去600多年,其流散、破坏的历史也有200多年。令人唏嘘的是,大典的编纂寄托了太平盛世的理想,最终的失散又映衬着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这本大书的命运,近乎国家命运的缩影。
1403年,明成祖朱棣称帝第一年,为了消弭“靖难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他希望以文化笼络人心,下令编纂一部大书。这部大书集纳天下七八千种图书,2000多人参与,总计11095册、22877卷、3.7亿字,定名《永乐大典》。
大典一直深藏在紫禁城,真正翻阅过的皇帝只有弘治和嘉靖两位。嘉靖帝确实十分喜爱大典,经常放一两本在案头翻阅。因为担心被大火焚毁,他甚至下令重抄一部,这次重录历时6年,完成时他已经驾崩三个月。后来就有传言,永乐年间的正本被带入了明永陵为他陪葬,因为自从副本重录后,正本就不知所踪了,如今传世的大典全都是嘉靖副本。除了“随葬说”,正本的下落还有多种传言,比如在万历年间紫禁城大火中焚毁,在李自成纵火皇宫时焚毁,以及藏在“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厚达6米的夹墙中等等。目前,被李自成焚毁的猜想为主流意见。
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副本在清雍正年间被贮藏在翰林院敬一亭,从那时起,大臣们陆续借阅大典辑录佚书,大典也陆续遭窃遗失。50年后,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清查,已缺失一千多册;嘉庆、道光年间利用大典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典丢失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已不足 5000 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剩余的大典绝大部分被焚毁,有人在废墟堆里就捡到了几十册。不识货的侵略者用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甚至做成马槽。略懂古籍价值的则趁机劫掠,与翰林院比邻的英国使馆得近水楼台之便,所得最多。
英法军官劫掠的《永乐大典》,成为大典流散国外的主要去向。
1996年,听说英国和爱尔兰新出现了零册,古籍专家张忱石前往两国实地查看。一位英国汉学家告诉他,这些大典一直存在老宅的阁楼里,几十年无人问津,也无人知晓价值,后来老人去世,后人清理旧物时才发现。2014年在汉庭顿图书馆发现的那册同样如此。那一册是美国传教士约瑟夫·怀廷1900年从中国带回家的,60多年后被他女儿随着其他藏书一起捐赠给了汉庭顿图书馆,被束之高阁长达114年之久。
清朝灭亡后,国家层面收藏《永乐大典》的行动,从1912年中华民国刚成立就开始了。作为公务员的鲁迅,还曾为《永乐大典》的国有化收藏出过力。
清末,内阁、翰林院仅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放在家里私藏。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图书馆就是他主管的事务之一。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促成这批书于1912年7月入藏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的开始。
通过政府划拨、海外送还、藏家捐赠、购买等方式,国家图书馆不断丰富《永乐大典》的收藏,至今一共藏有224册(其中62册暂存台湾),是海内外《永乐大典》最大的收藏机构。191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入藏,是1954年由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赠还,共52册。

(6月1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期间,工作人员通过情景剧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述《永乐大典》的故事。图/IC)
打捞失踪的古籍
《永乐大典》这一类的类书,对于后世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辑佚古籍。大典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但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年间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间已寥寥无几。
“古代书印得少,只有富人家才有,一经大火、战乱等,比较容易失传。”张忱石说。而类书就像一个移动的图书馆,保存了这些失踪古籍的内容,“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就是依靠《永乐大典》才失而复得的。
《旧五代史》于北宋初年编纂,清代前期已完全失传,乾隆年间依靠《永乐大典》“得十之八九”。1784年,《旧五代史》刊印殿本,入列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不过,据历史学家陈垣研究,清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因为政治用意也有篡改的现象。
清代编修另一部大型类书《四库全书》时,是依靠《永乐大典》辑佚古籍的高峰期,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被打捞出来。尽管如此,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
之后,从大典中打捞古籍的工作一直持续。例如,曾在国家图书馆任职的缪荃孙辑出《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等,赵万里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2004年,张忱石与几位学者共同编纂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出版,辑录了大典中失传的全部方志,共900余种,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张忱石还辑录了几本有趣的民间著作,比如宋代启蒙读物《金璧故事》,专门记录历代典故,后来放入《蒙学集成》中出版;以及元代的《净发须知》,是民间知识分子记录的关于理发的有趣故事。《永乐大典》的一个特征就是包罗万象,大量民间书籍也被收纳,集合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
在2013年入藏的那本“湖”字册中,有学者收集了22 位元代诗人的26首佚诗。这一册内容为含有“湖”字的诗文,主要来自唐宋元明四朝,收集的26首佚诗,连作为元朝诗歌总集的《全元诗》都没有收录。
《永乐大典》的辑佚颇具难度,主要依靠运气。这主要是因为大典的编纂体例十分特殊,并不是将现成的书合在一起而已,而把各种书拆散重编,分类的依据是韵和字。也就是“以韵为纲,以字系事”,每个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湖’字册下有‘东湖’条目,把各种方志里关于东湖的记录抄下来,再抄关于东湖的各类诗文等等,全部拆散了。”张忱石说。一个诗人的所有诗歌,会分散在不同的条目下。
张忱石认为,这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东一段西一段,要拼起来就难了。”所以辑佚的古籍残本居多,全本很难得。
1951年,藏书家周叔弢向国家捐赠一册“杭”字韵大典,竟然从中辑录出两本完整的书,堪称奇迹。这两本小书《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盛录》分别署名“灌圃耐得翁”和“西湖老人”,记载了南宋杭州城的风俗与文艺,都被完整收录。张忱石认为,从内容看,这两位作者不是一般市民,生活豪奢,常去各家私人花园,对皇宫的宫殿也了然于心,可能是皇室成员。后来发现元朝笔记里有记载,“灌圃耐得翁”确实姓赵。
这种体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了很多错误,“当时编书的人要先从书里摘取,然后誊写,嘉靖年间又重录,清代编《四库全书》再抄一次,每抄一次只会增加错误。比如唐代林宝编的《元和姓纂》,记载唐朝名门望族的事情,补充了很多名人事迹,后来失传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辑录了十卷,但明代拆得七零八落,辑录后错误太多,四库馆臣校了一次,学者孙星衍、洪莹又二校了一遍。到了近代,学者罗振玉利用唐代墓志又三校,后来岑仲勉再四校,才基本把错误校好。现在新出土了一些墓志,又可以继续校了。”张忱石说。
再造与新生
中华书局于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曾三次调查全球《永乐大典》保存状况,第一次由著名目录版本学者王重民牵头,此后两次都由张忱石负责。调查结果从第一次的730卷,到第二次的797卷,第三次调查截至2013年,又增加了21卷,超过400册、800卷。
总的趋势是发现新的零册越发困难。“以后可能还会冒出来,但大批出现不太现实。”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说,大典流失最多的年代是乾隆到光绪年间,被翰林院官员偷盗,从一万册锐减到不足千册。1900年遭侵略者劫掠时,翰林院只存800多册,因此更多的大典还是留在了国内。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认为,在国内发现大典的可能性非常小,查找的重点应是八国联军所属的八国。他提醒要利用藏书链来找书,比如苏联曾从大连图书馆取走55册大典,后来归还52册,剩余3册很可能还在当地。而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原藏的4册已不知下落,可能被带到法国去了。
等待的同时,国家层面启动了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比此前中华书局的影印出版规模更大,动员力量也更为强大。
2002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全球机构拿出大典底本,集中影印出版。“这是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大事,”任继愈倡议,“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慨允借用《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制版之用,用后归还,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截至目前,国图出版社已累计影印出版海内外233册,约占现存总量的56%。其中,中国大陆现藏的164册全部出版,海外13个收藏机构的69册也提供给了国图影印出版。这次出版采取仿真影印的形式,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几可乱真。
就在2002年前后,国图还启动了对大典的全面修复,为此定制了全新的书柜。现在,书柜里还有几十个空抽屉,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这是为更多回归的卷册预留的,包括新出现和回流的,也包括暂存台湾的62册。
1933年,北方形势趋紧,北平图书馆曾挑选《永乐大典》连同宋元精本、《明实录》等古籍南迁,在上海公共租界保存。上海沦陷后,部分善本被运往美国寄存,包括62册《永乐大典》。1965年,这批躲过战火的善本被运往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有权仍归中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