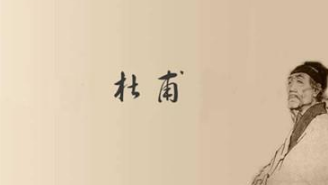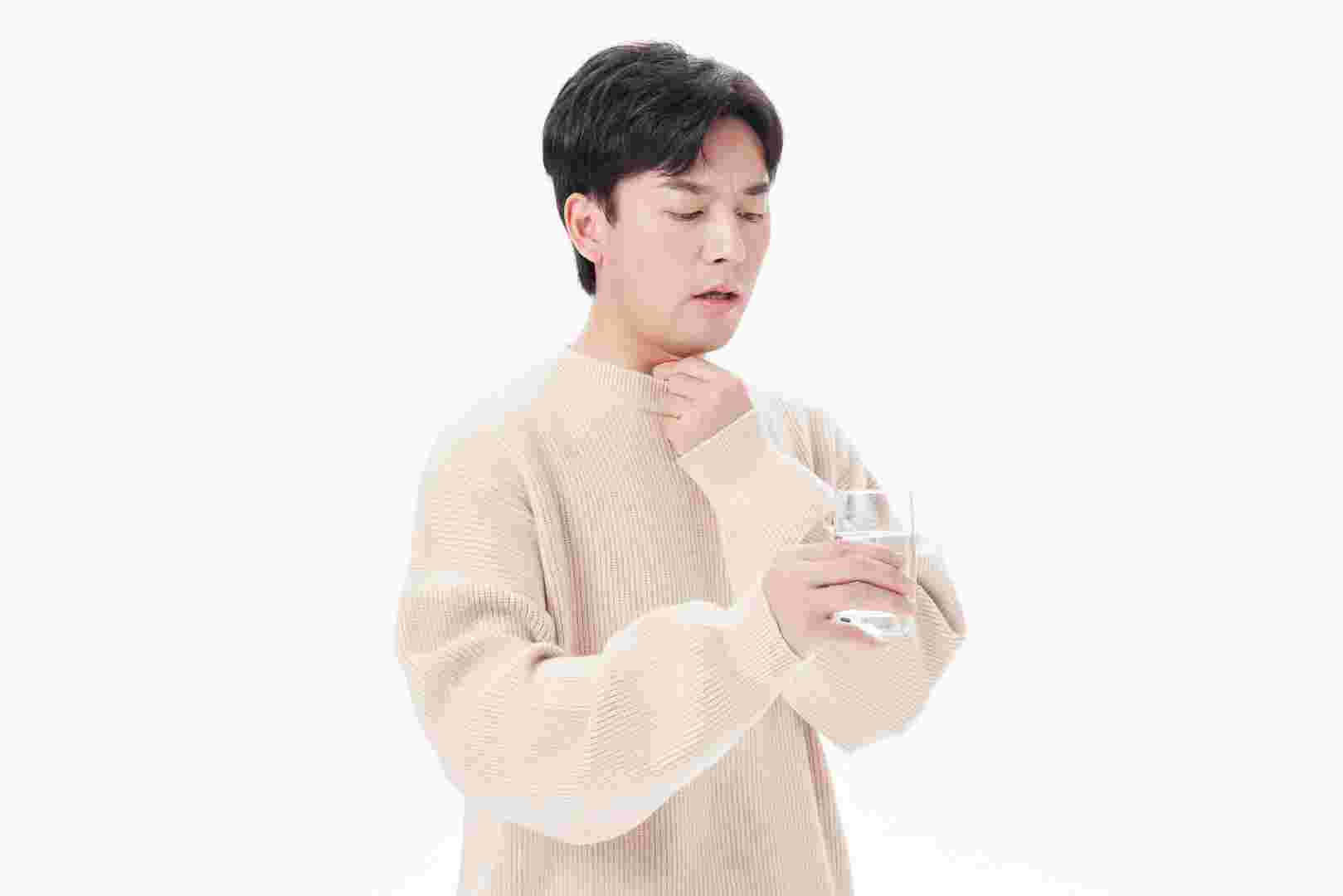四世同堂创作于20世纪多少年代(岁月里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创作于20世纪多少年代(岁月里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最主要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遗憾的是,这部“笔端蘸着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写成的‘痛史’和‘愤史’”,在老舍生前没有出版过全书完整本。因此,《四世同堂》浦爱德全译本的发现与回译,引起了学界与“老舍迷”的关注。

在美国期间,老舍与浦爱德合译了《四世同堂》英文版,题为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

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手稿
本文图片均选自《老舍评传》
《四世同堂》创作始于重庆、终于美国,是老舍主观情感与观念的投射。按照老舍1945年4月在北碚所作自序中的计划,《四世同堂》分三部,即“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1948年,一封信从美国纽约寄往日本。写信的人是老舍,收信的人是谢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在信中,老舍提及了第三部分的内容提纲:(一)大赤包死在狱中,她的西太后似的气焰至死也没改。(二)冠晓荷被日本人活埋,但本性难移,始终把日本人称为朋友。(三)瑞全回到北平,和高弟结婚。(四)招弟当了日本特务,被瑞全杀死。(五)钱默吟成为地下工作者的领袖,由于金三爷告密,被捕。(六)瑞丰被蓝东阳害死。(七)蓝东阳冻死在雪中。(八)瑞宣活动在地下工作中。
1949年,老舍在给楼适夷的信中谈道:“《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四世同堂》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但只连载到总第87段就“停更”了。“文革”之中,《饥荒》手稿不幸被毁,《四世同堂》中文本成为残本。1982年,翻译家马小弥根据美国哈考特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节译本《黄色风暴》回译了该书最后13段。198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单本《四世同堂补篇》的形式出版。《补篇》内容与提纲相比,除蓝东阳死于日本原子弹爆炸之外,基本可以一一对应,这个版本算是补上了残缺的故事。但由于哈考特出版社的编辑大幅删改,丢失了很多丰富内容,不能完整呈现《四世同堂》的叙事魅力与故事情节全貌。
幸运的是,2014年,翻译家赵武平确认浦爱德版《四世同堂》全稿在哈佛施莱辛格图书馆,这些材料被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30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同时,还有与翻译和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浦爱德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
由此可知,浦爱德版《四世同堂》英文原稿是浦爱德与老舍相互沟通产生的智力成果,具有无限接近《四世同堂》中文原貌的可能性。经过对读,赵武平发现英译第三部浦爱德版《饥荒》原始内容比哈考特版多出了九章,情节梗概虽未有大的更改,但情节的丰富与语言的多彩使老舍的审美风格与思想脉络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呈现。于是,浦爱德版《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的发掘与整理,成为老舍研究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赵武平将《饥荒》未曾发表过的第21章至第36章进行了回译,2017年9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署名赵武平译补的“完整版”《四世同堂》(以下统称“东方本”)。赵武平利用电脑词汇分析的方法,整理出“老舍词汇表”,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老舍的语言风貌。这种基于语料库的文学词汇分析方式具有现代科技优势,无论是文学词汇特征还是情节建构、人物刻画写作特征,在语料库检索分析中都能一目了然。因此,东方本注重细节,在人名、称呼、地名、常用词甚至标点等方面,依循老舍用词习惯,运用老舍“原词”建构内容。如老舍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的语气词多用“呕”和“什吗”,而非“哦”“喔”和“什么”,东方本亦延续此用法,与前文尽量融为一体。
东方本注重逐字逐句的翻译,出现了“她觉得自己既勇敢又聪明”“他假装受感动而低下脑袋,思索着所有这些既不一致又不舒服的问题”“经过这一次从来没有过的血的教训”等译文。然而,恰恰是这种力图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偏离了老舍在语言艺术中“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东方本希冀通过归纳运用老舍原词回归作品原貌,但是词汇的集合淡化了作品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审美形式,将复杂的文学创作机制简单化,产生了语言碎片化的瑕疵。
回译过程中,一个译面对应多个译心很常见。2017年,翻译、作家毕冰宾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翻译浦爱德版《四世同堂》中文稿佚失部分,2018年出版(以下统称“人文本”)。
比较来看,人文本修订了东方本存在的多处错译。比如,东方本中“她的嘴唇像肉铺里的娘们儿一样,已经习惯于染上鲜血。”原文为“Her lips looked like the ladles in butcher's shops that are used to dip blood.”单词ladles是ladle的复数形式,长柄勺之意,而非lady的复数形式ladies。人文本译为“她的嘴唇涂得血红,看着就像肉铺里血的长把儿勺子”,显然更为恰切。这种恰切不仅源于对词语更为精准的识别,还来自对老舍的深刻理解。老舍塑造了诸多善良宽厚的店铺掌柜形象,“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正红旗下》中开肉铺的王老掌柜便是个典型的勤劳、耿直形象。因此,老舍怎么会把妖艳无耻的女特务与肉铺老板娘画上等号呢?
再如,东方本中“拒绝吃共和面的时候,她的小眼要喷出火来,似乎是对家人说,她的小生命有自己的尊严——她不吃,希望猪与狗也别吃”,原文为“When she refused to eat Republic flour, the little eyes would spit fire as if to say to the family that she had the dignity of her little life —— she would not eat that which the dogs and pigs would not eat.” 在此,“which the dogs and pigs would not eat”与“that”构成的是修饰关系,其中并无“希望”与“别”这两个词。且在《饥荒》第七回至第八回中,老舍写道,凭粮证供应的共和面成为市民赖以生存的食物,“又酸又霉,又涩又臭”“人已变成了猪!”对此,人文本译为“她的小生命也有尊严,她不吃那个连猪狗都不吃的共和面”,似更为妥帖。
毕冰宾翻译的第二步是“在译文准确无误的基础上,译者要‘扮演老舍’”,即学者冯明惠提出的“译者须了解原作者及其所处之社会背景,更须体验原作者的心理过程”。毕冰宾敏锐地发现老舍原著中的京腔京韵并非表面化的市井北京话,而是富有北京特色的普通话,且随时代变化具有融合性与发展性,他倾向于把握老舍词句意蕴特点而非单个字词。
于是,在翻译行文风格方面,东方本与人文本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文本在叹词、称谓、时代性用词等细节方面未做到东方本入微的还原状态,但构成了“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京味儿。前文提及的东方本译例,人文本译为“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智勇双全”“他假装受到了感动,低下头去,他要厘清头绪,想清楚这些令他难受的事儿”“在这次空前的血的教训之后”,更符合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的特点。
钱先生的“悔过书”颇为考验译者功力,人文本运用了文白结合的译法,“世上本无完人,故人人都应时常认错。承认过失非但不可耻,反而可敬。”简明古雅,符合人物身份,堪称完美。东方本译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时时反省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缺点,没什么可耻的,相反倒是可敬的。”在语义上并无差错,却淡白如水,缺少了老舍推崇的“写东西一定要精炼、含蓄”。
《四世同堂》的回译是被作出了多种限定与期待的翻译,回译部分必须与已被奉为经典的前文语言风格、观念内涵一脉相承,否则就有狗尾续貂之嫌。
因此,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与表达决定了触摸历史长河中《四世同堂》散佚篇章的距离。两部回译本,分别运用了“词汇表复原老舍”与“扮演老舍”两种翻译策略,表征着对老舍语言风格、思想内涵的两种打开方式。可喜的是,两部回译本都把老舍《四世同堂》的原有设计脉络做了充分展现,既丰富了老舍研究的文献,也满足了“老舍迷”对《四世同堂》大结局的期待。